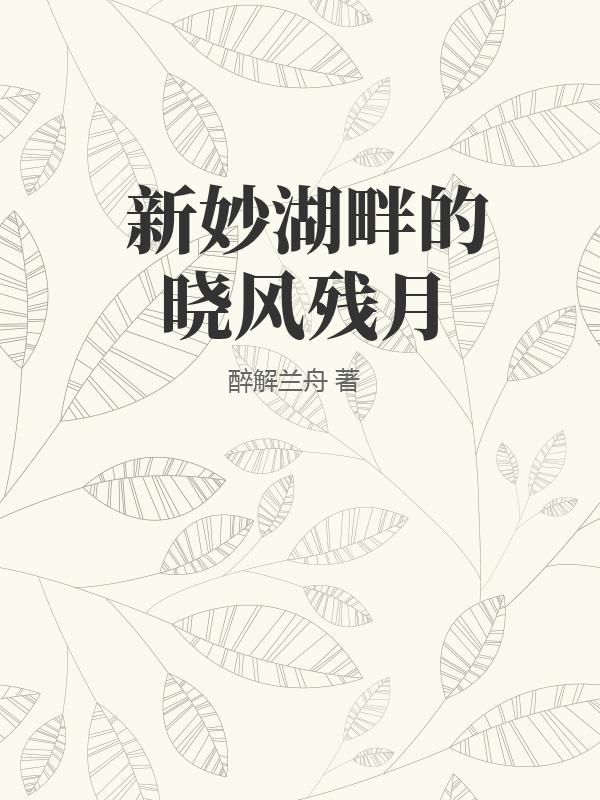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袁路生儿子袁建峰学习成绩优秀,成为永昌二中的尖子生,他在学校期间,与同班同学徐雪琴相互爱慕,但因谈恋爱被校方发现而受到处罚。后来袁建峰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而徐雪琴也在补习一年之后考入九江师专。两人毕业后都回到永昌一中教书育人,修成正果。
到了1999年,袁建峰的妹妹袁建英彼时也在永昌二中教书,见证了老永昌二中改名为新妙湖高中,以及之后新妙湖高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而导致的不可逆转的衰败与消亡。
进入新世纪之后,袁建峰的女儿袁晓雪从江西农业大学学成归来。在袁建峰以及老永昌二中校友们的支持下,接过关停空置的新妙湖高级中学的校舍,开创新时代的现代农业庄园——永昌共大农庄,让荒废了的新妙湖高中校舍,涅槃重生,重新焕发生机。
第1章 从新妙湖大坝说起
作为21世纪的新时代青年,袁晓雪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忆,大都来自于祖父袁路生的亲口讲述。从小就生活在永昌县城的袁晓雪,她对于农村的生活非常模糊,只有当节假日父亲袁建峰和母亲徐雪琴带着她和哥哥袁晓山,坐汽车回到乡下新妙湖畔的西港袁村时,袁晓雪才能接触到真正的农村。
似乎在袁晓雪的印象当中,每次回西港袁村,留在她记忆里的,不碍乎是跟着祖父袁路生一起在徐湾河边的菜地里摘菜,在老屋门前自家水井里打水洗菜,吃着祖母谭小红在老屋厨房黑乎乎的土坯灶台上做的饭。然后来到徐湾河上那座充满童年记忆的麻石桥上玩耍一番,再往西走过麻石桥,不远处就到了祖父心心念念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永昌分校——永昌二中——新妙湖高级中学。据说这也是父亲袁建峰和母亲徐雪琴曾经的母校,而且姑姑也一直在这所学校当老师,再远处就是美丽的新妙湖了。这些情景后来慢慢深入袁晓雪的灵魂深处,让她也与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那个懵懂的年代里,孩童时的袁晓雪每次回到西港袁村时,所经历的这些,留给她的记忆并不深刻,但这却几乎是祖父袁路生的全部生活,这位将毕生事业都献给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永昌分校——永昌二中——新妙湖高级中学,这所一脉相承的学校的退休老师。
西港袁村,这是祖父袁路生和祖母谭小红一直生活的地方,那里有丘陵起伏的田野菜地,有静静的小山岗,有潺潺不息的徐湾河,更有那碧水连天的新妙湖。据祖父袁路生介绍说,祖父和祖母结婚成家的往事;祖父祖母住的这幢土坯老屋,也是祖父年轻时亲手盖的;而父亲袁建峰,也是在这幢土坯老屋里出生的;还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永昌分校的诞生。每次祖父袁路生跟袁晓雪讲述以前的往事时,袁晓雪都好像是在听一个遥远的故事。
直到袁晓雪从江西农业大学毕业之后,她回到祖父袁路生曾经奋斗过的永昌共大——永昌二中校园,建设共大农庄,创业取得成功,她才回想要给共大农庄的陈列室里,增加一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的故事。这个时候袁晓雪很自然地想到了祖父袁路生,也只有这个时候,她才真正用心去聆听祖父袁路生,对她讲述这片土地以前所发生的许多故事,包括祖父自己的青春奋斗史、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永昌分校、永昌二中,以及袁晓雪的父亲袁建峰在高中时代的过往等。
这些故事后来都被袁晓雪一一记录下来,成为共大庄园历史陈列室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每一位来共大庄园游玩的游客,都能够熟知共大庄园,这座具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血脉的现代农业庄园,它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并将这种历史记忆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一种难以忘记的永恒。
在一个不太忙的炎炎夏日午后,袁晓雪把七十多岁的祖父袁路生,接到这勃勃生机的共大农庄接待室里,开始聆听这些有趣的故事。袁路生喝了一口袁晓雪泡的共大庄园浓茶,就从他年轻时参加建设新妙湖大坝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的青春时光和家族历史......
那是1960年的冬天,往日碧水蓝天的北庙湖,跟她的母亲湖——鄱阳湖一样,基本上干涸到底了,只有很小的地方才有一小片黄泥巴水面,大面积的湖床上留下了干巴巴的龟裂泥块和长须草。湖边寒风凛冽,湖中央淤泥很深,没几个人愿意冒着严寒,去下到湖床的泥巴里翻些蚌壳螺丝。刚刚20周岁的袁路生,高中毕业才半年,在家里参加劳动,就接到了村里生产队的通知,今年寒假又要出工一个月,跟村里的生产队一起,参加修筑北庙湖大坝。
原来永昌县根据江西省政府的指示,鉴于永昌北庙湖汊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省水利专家的筹划和准备,决定在1960年这个冬天,由永昌县政府组织全县农业劳动力,会战一个月,在永昌县的马鞍乡的马鞍山和南山乡的邵家山之间,人工修筑一条规模宏伟的拦水大坝,将鄱阳湖与北庙湖拦腰截断。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可以消灭北庙湖汊里的血吸虫;
二、可以留住北庙湖里的水,让北庙湖成为一年四季都是丰满的碧水蓝天,沿北庙湖的农田旱地用水,都可以得到灌溉;
三、可以在相对独立的北庙湖搞垦殖场进行水产养殖,造福沿湖人民。
永昌县政府随即在这个冬天做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总动员,要求全县农业户,以生产队为单位,每户出一名壮年劳动力,自带工具和干粮、被褥等物品,参与修建永昌县西部的北庙湖大坝和闸口,阻断北庙湖与鄱阳湖之间的湖水。
北庙湖是永昌县境内的一个鄱阳湖支湖,面积有40多平方公里,以前和鄱阳湖是连通的,没有任何阻隔。自从1960年袁路生参与会战修建了北庙湖大坝之后,北庙湖才成为独立的支湖,所以这座北庙湖大坝的意义十分重大。
北庙湖的名字,是因为北庙湖南侧清水乡境内有一座北庙,是为纪念晋征西大将军陶侃之母,湖因庙而得名。后来在1962年,北庙湖大坝已经修筑完成两年后,原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来此巡查,以北庙湖大坝建成后,对永昌社会经济影响巨大,寄希望永昌人民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以“北庙”永昌方言谐音“不妙”,于是亲自改名为“新妙”,寓意新时代美妙之湖,所以后来沿称新妙湖。
那个年代,永昌县的老百姓早就习惯了春夏秋三季在生产队里劳动,冬天按照政府的安排,义务出工,兴修各地水利,为来年的农业生产做保障。袁路生是家里的老大,父亲在两年前因为喝醉酒失足,掉入徐湾河出现了意外,母亲谭桂芝又是小脚,做不了这些重活,底下一个弟弟水生年纪才17岁,两个妹妹也未成年,银花15岁,杏花才13岁,因此20岁的袁路生早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前年冬天他就参与过苏山水库大坝的修建,寒冬腊月天在荒郊野外干活,一干就是一个多月,身上几乎掉了一层皮。听说这一次又要修建北庙湖大坝,工程量比苏山水库大坝要大得多,但硬着头皮也得上。
袁路生在家收拾停当,就背起母亲谭桂芝准备好的铺盖碗瓢大米干菜油盐等生活用品,以及铁锹竹筐扁担等工具,按村里生产队的统一安排,在腊月初十这一天一大早,和村里其他出工的人一起,冒着肆虐的寒风,坐上由徐湾乡政府统一安排的大卡车,一起去往北庙湖下游的马鞍乡马鞍山脚下,在那里修筑北庙湖大坝。
这条准备修建的大坝,是从永昌县南山乡鄱阳湖岸角上的邵家山开始,一路笔直往北,跨过鄱阳湖,直到马鞍乡的马鞍山脚下,需要修建长1.9千米、高23.5米,宽20多米,并同时修建水闸控制北庙内湖和鄱阳外湖的水位。大坝修好之后,坝顶还规划修建双向两车道的马路,以方便南山乡和马鞍乡南北往来,极大缩短了马鞍左蠡苏山等乡镇的人们到永昌县城的路程。
大坝指挥部指示,为了节省劳力,如此巨量的土石方工程,按照就近取土原则,在大坝两头的马鞍山和邵家山周边爆破山石、土方,然后由各生产队的劳动力肩挑脚拉,将土石方运到指定的大坝工地。在上世纪60年代,全都是靠永昌广大农民用手挖肩挑,一抔土一抔土地挖运堆积到这座雄伟的大坝上,没有任何挖土机、推土机、渣土车之类的机械,艰苦可想而知——袁路生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也是他日后跟孙女袁晓雪经常讲的话题,并且在不忙的时候,带着袁晓雪去新妙湖大坝走走看看,言传身教,告诉她,这条大坝并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点点筑成的。
在这个寒冬腊月的鄱阳湖里,袁路生和上万农民兄弟一起,义无反顾地自带粮食、工具,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干着最艰难的工作,而且没有工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永昌老表们都斗志昂扬地向鄱阳湖伸出了勇敢的双手。
经过一个多月的筑坝出工,一座雄伟的人工土筑堤坝锁湖为池,横断鄱阳湖上,让新妙湖获得了新生。袁路生终于可以和村里三十多个壮年劳动力一起,坐着政府组织的大卡车,兴高采烈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风摧雨磨,袁路生跟村里其他劳动力一样,满脸风霜,双手也磨起了老茧,一身旧蓝色的棉袄棉裤,头戴一顶黑色卷边的挡风帽子,回到新妙湖畔的西港袁村自己家里。
母亲谭秀芝看着大儿子辛苦成这个样子,一阵心疼,看着家里大大小小5口人,所有的重担都要这个大儿子来挑,老二袁水生虽然过完年年也才刚刚18岁,但从小就不大懂事,没有老大那样的担当,只能跟着母亲在村里生产队里挣些工分,老三银花和老四杏花还没成年,那么多吃饭的嘴,日子过得很艰难。
大儿子袁路生从小读书就很刻苦,他是少有的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后,虽然说在家里参加劳动,但袁路生有文化,被村长袁炳林当成宝贝疙瘩,村里很多需要书书写写的东西,全都请袁路生代劳,而且这样也算正式工分,那时候农村里读书人很少,村里都把袁路生当成宝贝了。要不是老头子前年醉酒失足坠入河里出了意外,家里的日子应该还好过。谭秀芝虽然还只有50多岁,但农村的艰苦和沉重的负担,早就把她熬成60岁的老太婆了。今天村里人都知道修大坝的劳动力要回来,家家户户都跟过年一样,重新给他们补过个年,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一大早谭秀芝就安排老二和大女儿去队里继续出工挣工分,小女儿帮自己在家里做顿吃的,给大儿子袁路生接风,也算是犒劳一下。
母亲谭秀芝其实也是个缠过足的苦命人。袁路生小时候常常听母亲谭桂芝给他们讲,她娘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平时厨房里有很多佣人做饭,家里有许多长工在田里干活,苏山脚下的谭家咀100多亩良田以前都是她娘家的。她的爷爷是在景德镇做瓷器生意的,头脑活络,走南闯北,思想也开阔,在景德镇做生意发财后,回到谭家咀置地盖房,又从村里手里买了大量的良田,成为村里仅有的几家地主。
据说当年母亲的娘家在她们村还不是最富有的,还有两家人比母亲娘家还要富有,据说最富有的那一家人,嫁女儿的时候,陪嫁之一有18把金剪刀,由此可见一斑,比之现在的土豪一点也不逊色。据说谭家咀这几家富裕人家,无一例外,都是结帮在景德镇做陶瓷生意发家的,只是后来结局不一样。
后来清末民国初年,战乱频繁,加上外祖父不善持家,酗酒赌博,吸食鸦片,导致家境中落,家财散尽,只剩下那座空荡荡的棋盘屋大宅院,似乎还在诉说它曾经的繁华。袁路生小时候经常去舅舅谭桂清家玩,虽然舅舅家早已经没落,但从整齐划一的大宅院,依稀可见昔日的荣光。母亲谭秀芝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外祖母四处流浪,后来流浪到现在的西港袁村,被袁路生好心的爷爷奶奶一家人收留,母亲谭秀芝也就顺理成章成立袁家的童养媳,那时候爷爷奶奶也是殷实的人家,虽然算不上地主,但自给自足,温饱有余,解放时被划为中农,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不过母亲娘家也因祸得福,当年外祖母带着年幼的母亲谭桂芝离开谭家咀之后,舅舅谭桂清从小就在村里靠吃百家饭长大,解放后,他们家很自然地划分成贫农,算是守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幢棋盘屋大宅院。而村里另外两户人家,却因为是地主,被没收了家产和农田,分给了村里的贫苦人家,令人感慨不已。
母亲谭秀芝自小成为袁家的童养媳之后,跟着奶奶相依为命,奶奶视母亲谭秀芝如己出,婆媳关系融洽,为袁家继往开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奶奶虽然一辈子在农村,日子过的很苦,但穿衣服向来讲究干净整洁,常年几身衣服洗了又洗,虽然没有换新的,但从来不邋遢。头发梳得很利索,虽然白头发越来越多,但到老还有一些黑发。床上的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房间的家具虽然陈旧,据说流传了多少代,但常年擦得干净发亮,一点都不显得沧桑。奶奶这些朴素优良的家风,不仅影响了母亲谭桂芝,也影响到袁路生和弟弟妹妹们,携手渡过了那个艰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