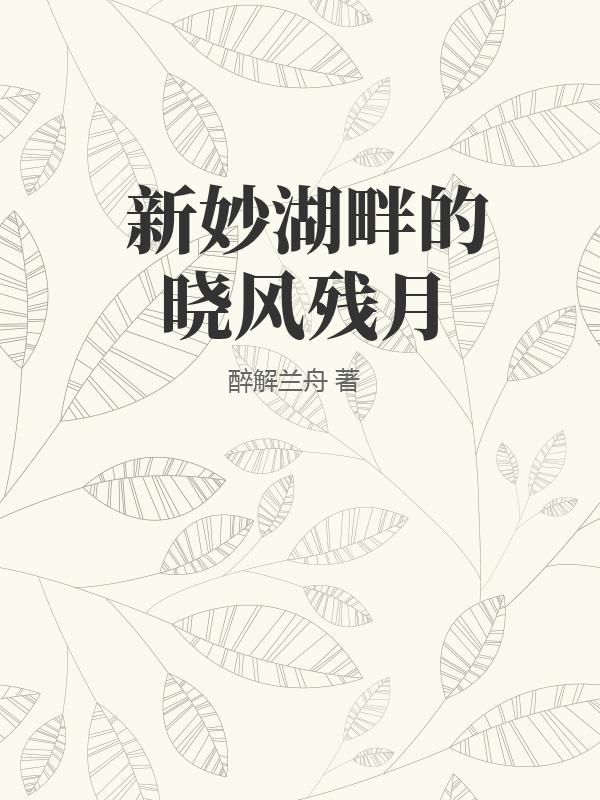1961年的春天,对于袁路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不仅从沉重的冬季外出务工劳动中得到了锤炼,逐渐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而且在这次新妙湖大坝出工中,表现良好。他是村里唯一一个高中毕业生,很有文化,不仅像村里其他农民一样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的,村长袁炳林还安排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承担队里文书的写作工作,把村里这次冬季出工筑坝的总结、工分、向上级报告等内容,袁路生按照要求,把队里的材料全部写出来。报到徐湾公社后,得到公社李书记的极力赞扬。
正巧隔壁东星大队办的小学缺少一名老师,公社李书记找到西港袁村村长袁炳林,点名要求袁路生去东星小学当老师,要求赶紧去办,因为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李书记数来数去,全公社也就袁路生最合适。这天傍晚,刚刚点上煤油灯,村长袁炳林从徐湾公社李书记那里,带着一张空白的履历表,赶到西港袁村后,径直来到袁路生昏黑的土坯三间老房子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袁路生:“路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隔壁东星大队缺一名老师,公社的李书记这次点名,要你去东星当老师,整个公社现在闲在家里的,就数你的学历最高了。”
“炳林叔,你不是在逗我吧?”袁路生没反应过来,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他家在大队和公社都没有什么熟人,也没有关系,做梦都不敢想能去当老师。
“我都快六十了,这种事情,还能骗你?”袁炳林微笑着点了点头,拿出这张空白的履历表,接着说:“今天下午公社李书记专门把我叫到乡里,向我了解你们家的情况,他对你的报告很赏识,这次点名要你去东星大队当赤脚老师,工资由他们东星大队发,以后有机会转成国编老师。”
“那太好了,感谢炳林叔。”袁路生满心欢喜地接过袁炳林手里的履历表,放到客厅桌子上的煤油灯跟前仔细看。
“今晚抓紧把这张表填好,明天一早交给我,我签完字,再找大队书记签完字,再送到公社李书记签字,这事就成了,估计一两天就办好,你抓紧做好准备,过两天通知下来了,你就带通知去东星小学报到。”
“感谢炳林大哥,帮我家路生找到这么好一份工作。”谭桂芝倒了一杯茶水递给袁炳林。
“大妹子,你家路生很优秀,能文能武,未来不可限量,以后的日子不要太愁,路生以后当老师了,平时要去学校上课,不用再到队里出工了,在我们村算是出头了。”袁炳林和路生的父亲以前关系很好,解放前曾经一起参加过游击队,打过鬼子,路生的父亲出意外后,对他们家也有些照顾。
“感谢炳林叔夸奖,我晚上写好这张表,明天一早给你送过去,后面还得麻烦你签字再送到大队和公社呢。”
“不妨事,你晚上慢慢写,后面的手续我来办,这两天就要准备好,学校还有两天就要开学,等介绍信下来了,我就给你拿过来,你就可以去东星小学报到了。”袁炳林讲完,转身就往外走。
“好啊,我这就开始填表,炳林叔慢走。”袁路生激动得浑身都有些发抖,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兴奋。
袁路生把村长袁炳林送出门,马上坐下来按照要求,填好了这张履历表,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过了两天,公社李书记果然签字批准了袁路生的老师申请,袁路生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徐湾公社,从李书记手里接过介绍信,正式成为一名赤脚老师。
五十多岁的李书记拍着袁路生的肩膀,一边用殷切的目光对他说:“路生啊,从今往后,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一定要把我们公社的娃娃们教育搞好,让他们学到有用知识,你肩膀上的担子可不不轻啊。”
袁路生第一次和公社李书记单独谈话,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感谢李书记,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我们徐湾公社下面的村里文盲太多了,大多数人大字不识一个,以后的娃娃们可不能这样,只有通过读书,多学知识,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公社里像你这样读到高中的人,真的是太少了,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现在虽然是赤脚老师,过几年等有条件了,再想办法转成国编老师。”李书记殷切的目光和诚恳的话,一直是袁路生日后走上教师这个岗位的最原始动力,也成为他日后在新妙湖畔执教一生的鞭策。
从公社回来后,袁路生就开始收拾东西,因为第二天就要上学校报到了。虽然不是国家编制,但由于是大队聘请的老师,以后不用去生产队出工,大队也会按照“工分”标准,支付袁路生的教师工资,这个消息传回到西港袁村后,整个村里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
第二天就是东星小学开学的日子,早春的阳光已经悄悄地滋润着新妙湖畔的这块土地,袁路生背着简单的行囊,带着公社开的介绍信,兴致勃勃地沿着新妙湖畔的田埂小道一路往东走,来到三、四里路开外的东星大队小学报到,正式成为一名赤脚老师。
在学校教室办公室里,接待袁路生的,是一位中年男老师,这位老师看上去四十多岁,国字脸,带着一副黑框眼镜,一身蓝色中山装,和袁路生自己一样中等身材,看到年轻的袁路生背着铺盖行李走进来,立即站起来问:“你是西港袁村的袁路生老师吧?”
“老师,你好,我是袁路生,今天来学校报到。”袁路生拿出介绍信,递给中年男老师看。
“昨天公社里已经派人通知我了,我姓徐,是东星小学的校长,欢迎袁老师的到来。”徐校长走上前一边握手,一边自我介绍。
“徐校长好,以后请多关照。”
“我们学校去年底放假时,三年级的语文老师调走了,一直在找公社要人,李书记的办公室快被我踏破了,前几天李书记就推荐了你,说正在办手续,让我等消息,现在终于等来了,以后我们都是同事,相互关照,把这个东星大队娃娃们的教育抓好。”
听了徐校长的自我介绍,袁路生了解到这位徐校长也是大有来头,原来他是徐湾公社所在的徐湾村人,解放前在南昌读过大学,解放后因为家庭成分原因,被分配到东星小学教书,后来公社又安排让他当了这所小学的校长,负责这所学校已经有好几年了。
徐校长领着年轻的袁路生,把学校几位老师一一作了介绍,又在东星小学里到处走了走,介绍了学校的大致情况:东星小学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地处新妙湖与徐湾河交汇处东北角,东星村边上,以前的一片乱葬岗坟地,解放后公社统一安排,平整了这块乱葬岗,迁坟、平地基,建了两排低矮的房子,以及配套的办公室、教师宿舍、食堂和厕所。学校没有围墙,分设三到五年级一共三个班,五位老师。整个东星大队周边五六个村子的小孩,都会到这里来上学读书。而小学一、二年级,因为考虑到各个村子里的孩子都比较小,分设在各村子里的祠堂里,方便低年级的小孩子上学,大队里会安排各个村里的赤脚老师在他们村里负责一、二年级的教书。
天生胆小的袁路生,听到徐校长介绍学校的情况,有些皱眉头,从小就害怕经过乱坟岗,现在竟然在乱坟岗上建的学校教书,白天还好,晚上会不会有些吓人。
徐校长看到袁路生脸色不好,笑着手:“小袁老师也这么胆小?我们学校晚上有3个老师,包括我自己都在学校里住,只有两个本村的老师回家,我已经安排别的老师,给你收拾了一间宿舍,就在我隔壁。”
“听上去确实有些害怕,白天还好,晚上要是一个人住的话,确实不敢。”袁路生有些难色。
“刚开始不习惯,过段时间就好了,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不会怕那些东西,以后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徐校长开导他。
徐校长的热情,很快就打消了袁路生的疑虑。就这样,袁路生接过东星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开启了伴随他一生的崇高职业。而这位徐校长,则成为袁路生教师生涯的领路人,他把自己曾经在省城大学里学到的很多知识,在工作中也不断灌输给了袁路生,让袁路生自身的知识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徐校长也很尊重这个诚实稳重的年轻人,两人后来成为忘年之交。甚至多年以后,袁路生的儿子袁建峰与徐雪琴的早恋问题,也是徐校长退休以后,从中斡旋,劝说徐雪琴的父亲徐汉生,才成就了一段佳缘。
东星小学离西港袁村有四、五里路,隔了两个田垄和几个小山岗,袁路生跟其他几个外村的老师一样,平时周一到周六,都留在学校里住,只有周六傍晚放学后,才能赶回西港袁村。
袁路生当上老师以后,两个年幼的妹妹银花和杏花,对哥哥袁路生的印象却渐渐比较模糊了,两位妹妹的记忆里,袁路生总是周六一天晚上回家来,周日晚上就得赶回学校去,在家里待上一天,周日帮家里出工,再挣点工分。每次都是匆匆来去,像一阵风,一会儿就走远了,一家人待在一起的机会很少。
袁路生在东星小学待了4年多,后来又由于表现突出,被公社来回调动,在徐湾公社下面好几个大队的小学都教过书。那些年哥哥袁路生到底在哪些小学教书,袁银花和袁杏花两个年幼的妹妹从来没有出过门,当然不清楚,只是感觉他换了好几个学校,而且越换越远。
周末大哥袁路生回家来了,在家干一天农活,到生产队出工,或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忙乎,或砍柴、积肥之类。干活之前要先换一套下地的衣服,返校的时候再换回学校的衣服。当时,周末休息一天,星期天傍晚要返校,晚上校长要召集老师开教学会,有时也可能是集体政治学习。大哥袁路生为了多干一些活,要忙到很晚,天色快要落暗,才从田地里回到家,把家里的水缸灌满,才收拾一下,趁着夜色返校。
每年快到年关,哥哥袁路生用扁担挑着一担行李回家来,其中必有一床用麻绳扎的整整齐齐的被子,回家后再打开,将被面洗干净;一床用报纸包好的棉花褥子,同样用绳子扎整齐,吊在房间的横梁上——这都是母亲谭桂芝从小教育的好习惯。大哥袁路生有时还带一些吃的回来,比如说苹果,喷香喷香的,非常好吃。虽然是哥哥袁路生孝敬母亲谭桂芝的,但弟弟妹妹基本上都包圆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自从哥哥去当老师以后,每年冬天,他们学校都会分发两蛇皮袋子的木炭,从那以后,冬天烤火,袁银花和袁杏花再也不用去山里面捡松球来烤火了。
过完年之后,大约元宵节前几天,大哥把吊在横梁上的棉絮解下来,缝上干净的被面,照例用绳子扎的整整齐齐,弟弟袁水生和妹妹袁银花袁杏花又眼巴巴地看着大哥用扁担挑着行李和那床被子,去到他们很模糊的地方去教书。母亲谭桂芝往往会叮嘱一番,然后让弟弟袁水生帮哥哥袁路生挑一脚,送到村陇里两里路开外才回来。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袁银花和袁杏花还清楚地记得:当了老师的大哥,是没有暑假的,学生们放假了,老师们则由公社统一安排下到各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他们同吃、同住,一起下地、一起劳动。一年之中,大哥在家里的日子只有寒假和周末,而且他还要下地出工,因此一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少。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64年的春天,看着已经24岁的大儿子,还没有成家,母亲谭秀芝有些着急了,因为村里跟他岁数差不多的人,基本上都结婚了,24岁对于农村人来说,已经是大龄青年了。虽然说大儿子袁路生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出力少,挣的工分还多,以后一辈子都不用受苦受穷在土里刨食,但大儿子的终身大事终究不能耽搁下去,何况老二袁水生过完年也21岁了,两兄弟都面临要成家,老三银花也有18岁,老小杏花16岁,家里现在不缺劳动力了,基本上都能在队里挣工分,是该考虑给两个儿子讨老婆了。
1964年大年初一,春天快要来了,寒中带暖的春风吹过新妙湖畔的柳树,千丝万条地摆动,湖洲上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长须草,蓼子花也到处都是,岸上的田埂也露出了绿色的嫩芽,大地回春,一片生机勃勃。这天上午,谭秀芝带着儿女们回到娘家谭家咀,给哥哥谭桂清家拜年。谭秀芝娘家在苏山脚下,虽然到鄱阳湖边还有一段路程,但她娘家在苏山那有一个大水库苏山水库,是前两年刚刚建好的,水库里有鱼,高高的苏山上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野果蘑菇,应有尽有,只要家里勤快,吃饱饭是没问题的。
吃过午饭,坐在谭桂清那座气派的棋盘屋客厅门口晒太阳拉家常,谭秀芝用手指着远处两个到处看风景的儿子,对哥哥谭桂清说:“哥哥,你看你这两外甥,过完年后,一个24岁了,一个21岁了,还没有找老婆,我一个妇道人家,操不了这个主啊,怎么对得起他家老头子,哥哥有没有合适的女崽俚做媒?”
谭桂清看着渐渐长大的两个外甥,这个尝遍人间冷暖的庄稼人,瞬间明白妹妹谭秀芝的难处,当即就跟妹妹谭秀芝讲:“秀芝,我们谭家咀村南头的谭友林,也是个忠厚人家,知根知底,关键是他有个小女儿谭小红,还待字闺中,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在村里是个一等一的劳动力,山里水里田里地里,又勤快又能干,过完年就21岁了,我看跟我们路生很般配。年前我和谭友林在苏山上砍柴火时就开玩笑说,他家谭小红要是嫁人了,他家就少了一个好劳动力。当时谭友林就叹气说,周边村里也没个好小伙子,有的话,让谭桂清当媒人,赶紧把谭小红嫁出去,女孩子家大了,就留不住,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就希望找个好人家嫁了得了。要不中午吃完饭,下午把谭友林邀过来说一说?”
“谭小红,这女崽俚我也见过,很勤快一个人,长得也不赖,又是我们谭家咀娘家人,如果能讨他家女崽俚做儿媳妇,我这个婆婆以后日子好过多了。”谭秀芝眼前一亮。
“那好,我一会儿就上谭友林家,跟他说说看。”谭桂清当即拍板,自己马上动身去找谭友林。
果然没有一盏茶的功夫,谭桂清就就村南头跑回来,满脸红光地说:“秀芝、路生,走去谭友林家,他们一家人都在,谭友林一听是我外甥路生,马上就同意了,还催赶紧带外甥过去坐坐,今天大年初一,机会难得,换着平时大家都忙。”
谭秀芝这才跟儿子袁路生讲:“路生,我们去趟你远房舅舅谭友林家,他家小女崽俚谭小红你小时候也见过,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又勤快,一会儿就过去看一看,看好了,你跟谭小红就处一年,明年开春结婚。”
袁路生脸上刷的一下子红了,有些难为情:“妈妈,这...这样不好吧?”
“男崽俚看老婆,一定要大方,不要害羞,长大了谁都得娶媳妇,以后让你媳妇孝敬你娘,这个谭小红是舅舅村子上的人,知根知底,娶了她,她以后对你娘,会跟自己娘一样好。”谭桂清当即教育大外甥。
“你们上谭友林家,把这包冰糖和大枣子带过去,正月初一上别人家,可不能空着手。”袁路生的大舅妈连忙拿着母亲谭秀芝带过来拜年的礼物拿出来,塞到谭秀芝的手里。
“谢谢嫂子,还是你想得周到。”谭秀芝接过布袋子,然后就和谭桂清一起,拽着大儿子袁路生往村南头谭友林家去。
袁路生平生第一次看女崽俚,确实有些害羞,别看他在学校教书都已经三年了,在学校面对的都是小学生,加上这几年都在想着撑起这个家,个人的感情问题完全是空白,这次被舅舅这么一讲,袁路生也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跟着舅舅和母亲一起往谭友林家走。
谭友林和谭桂清隔了很多代,基本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同村人了,但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谭家咀村里人也都知道谭桂清的大外甥是老师,文化水平又高,家里这几年过年贴的春联,都是出自谭桂清的大外甥之手。谭桂清边走边看着清瘦而又有朝气的外甥,如果以后能成自家村里的女婿,亲上加亲,自己这个做舅舅的都很有面子,因此心里也很高兴。
谭友林的儿子早已经成家了,大女儿谭秀红也出嫁了,现在就一个小女儿谭小红待字闺中。谭友林对袁路生早就了解,这个斯文后生,很会读书,又是老师,如果能把小女儿谭小红嫁给他,谭友林是非常愿意的。
“友林哥,打扰你了,今天带着我的崽俚上门看你家小红。”袁秀芝走进谭友林土坯三间瓦房的客厅,幽暗的前厅里也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正中一张大四方桌,两把椅子摆设在两边,前厅一个木质简易屏风上贴着一张山水风景画,客厅两边都是农用工具和长条木凳。谭秀芝把手里的冰糖和大枣放到前厅的四方桌子上。
“哎呀,这么客气,都是自家人,这是路生吧,小伙子几年没见,现在成熟多了。”谭友林今年六十,花白的两鬓和皱纹,掩盖不住他发自内心的喜悦。
“舅舅好,打扰你们了。”袁路生有些羞涩地回答,这可能就是未来的老丈人了,袁路生虽然见过不少风浪,这次还是有些不自在。
“来,不要站着,坐下说话,”谭友林回头喊在厨房干活的小女儿谭小红:“小红,你姑姑和哥哥来了,赶紧过来倒茶。”
“嗯,姑姑好,哥哥好。”从西侧土坯厨房走过来一个穿着粗花布棉袄的小姑娘,头上用红头绳扎了一个大辫子,圆形脸蛋,虽然有些土气,但仍然透出一份青春的秀气,看到谭秀芝和袁路生,脸上红扑扑的,有些害羞,泡了两杯土茶水递给谭秀芝母子俩,红着脸转身就跑回厨房。
“女崽俚有些怕丑,没有见过世面,我这女崽俚除了没上过学,其他都好,无论是做饭洗衣服喂猪,还是下田里割稻子种秧,还是到苏山去放牛采茶叶捡蘑菇,几乎什么都干。”谭友林担心袁路生看不上自家女崽俚,赶忙解释。
“哥哥你客气了,小红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好处没得说,都跟我家路生讲过了,以后亲上加亲,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谭秀芝很满意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直接地表态。
“舅舅,我听我姆妈的,但我家情况不好,小红如果来我家,怕是要吃苦,我们家比较困难,弟弟妹妹都还小,都要照顾。”袁路生心底里也能接受谭小红,但他也需要把自己家里的一些情况跟这远房的堂舅讲清楚,千万不要勉强才好。
“说的哪里话,我们两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你爸走了之后,你妈也难,我家小红很能照顾人,又勤快,你又有那么多文化,只要你不嫌弃我家小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谭友林自然很满意这个未来的女婿,一锤定音,后面就和谭桂清、谭秀芝兄妹商量,媒人就由谭桂清来做,什么时候订婚,什么时候去公社登记,什么时候办结婚酒。
袁路生插不上嘴,听到这些有些难为情,只能尴尬地坐在旁边,喝着谭小红泡的茶水。虽然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谈恋爱一说,但两情相悦是人的本能,袁路生对谭小红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可能这个小姑娘能给他带来踏实感和归属感,可能也说不上来,两家的长辈都已经表态了,自己也不排斥,这个婚姻基本上也就成了,后面就等着订婚、登记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