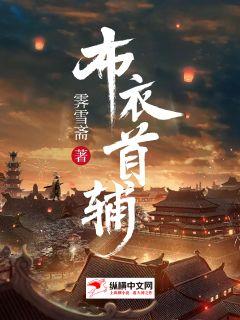靖武八年暮春。
“闪开、快闪开!”
官道上,两名红衣黑斗篷的骑士策马狂奔,马蹄踩在坑洼处泥水四溅,吓得道旁摆摊的、看货的、行路的、交谈的避之不迭,惊叫连连。
“两个死鬼,这是做啥哩?路上有人也不顾,急着去投胎么?”有人愤愤道。
“非也,非也。此乃缇骑,来捉人的。”一个穷秀才摇头道:“尔等不知?
去岁十一月太皇太后驾崩,国丧期间应天府竟有士子携妓宴饮,被人告发下狱。
那应天提学陈大人就住在本县机杼巷,他有管教不严之责已被罢免关押。
想必这二位是奉命往余干县里,索拿陈大人家眷的!”
“莫胡说!”旁人对他的卖弄付之一嘁:“前日村里念告示,还在说太皇太后仁慈,叫皇上免了大水过后受灾各县的农税……。”
“想你等乡野村夫如何知道?”秀才脑袋摇得更夸张,故作神秘道:“重阳节后太皇太后旧疾复发便未再参与朝会。
我京中亲戚来信说太医院日日进宫请脉,迁延一月便驾鹤西去了。”
“啊?”众人大惊:“才一月……?怎么这样快?”
“轰隆隆”一阵雷声响过,众人猛地缩了脖子。
有人轻声告诫:“都小声点吧,老天听见,要不高兴喽。”
抬头看天,眼见云幕黑压压地过来,远处透亮的地方打着闪,原本冰凉的风忽而潮湿了。
“唉,回家吧,买卖做不成喽!”卖竹编的小老儿收起物事,瞧着天色双手合十念叨:
“但愿明日艳阳高照,不然咱小百姓还不知上哪里换油钱呢。这世道才稳了多久,可别再变喽!”
说完,他匆匆系好蓑衣,挑起扁担,踩着道沿颤巍巍地家去了。
刚才还热闹的官道忽地静无人响,只有风头卷起落叶,渐渐被乌云拢进无边的黑暗。
------------------
春已暮、夏将至。
往年这季节大的雷雨很少见。
豆粒大的冰雹先行而至,人们措手不及,地面被砸得“噼啪”乱响。
城西北的李府宅中,丫头婆子老妈妈们正扎手跳脚地忙着关窗闭户,四下里跑得如受惊的鸭群。
若在平时,家主早气昂昂地在廊下高声呵斥:“慌什么?我李家好歹出过礼部主事老爷的,成何体统?”
不过今日,老爷太太们显然有更重要的事,顾不上她们了。
“三爷这消息……,肯定?”问话的女人声音颤抖,手里绞着月色的丝帕,保养良好的手指关节有些发白。
“二嫂,衙门书办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该是没跑的。”她右前方坐着的微胖男子习惯性地摸着下巴上的短须点头。
“既如此,怎生是好?离硕儿成婚只两月,陈家大姑娘可是块种瓜得瓜的好田地。
这门亲事已在县里传扬得人尽皆知……。
如今她娘家出了此等事,连休书都不得写(见注释一),若落下口实碍着五郎的运数,可怎么好!”
二奶奶高氏急得跺脚,伸手拿手帕子揩眼角便骂:“那害眼疾的劳媒婆子,做的什么好生意,我早说不该找她!”
“弟妹且莫慌,好歹我李家还是出过礼部主事的!”
坐在上手的长房大老爷李肃见她口不择言心中不悦(见注释二:),咳了声开口安慰:“纵然缇骑来拿,值此国丧期间,遇上陛下开恩降等也有的。”
他见妇人眼中露出些轻松,又一转道:“不过陈老爷想躲过此灾怕是不能。太皇太后故去,要么皇帝亲政,要么太后观政。
无论如何这等案子都不可推翻,岂有让陛下背不孝之名的道理?”
当今在位的靖武帝赵拓登基时只有九岁,因这缘故朝里曾因立年幼的夏王(赵拓)还是立庾太妃所生的成年皇长子赵挺大吵。
结果是赵挺亲自到朝堂,指出立嫡在先并严厉斥责了立长派的野心,站在太皇太后和圣母皇太后一边支持弟弟继位,随即自己便去范阳(涿州州治)就藩。
这场闹剧终于以范王让嫡落下帷幕,因此皇帝最敬重的人便是当年一力维护自己的:太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和范王这三位。
所以李肃说官家不可能推翻太皇太后大丧期间发生的这起案子,何况它已经尽人皆知。
“啊?照大伯如此说,这……。”高二奶奶的脸顿时又苦下来。
“此事咱们急不得,先要看陈家自己造化。”大老爷摇头道:
“我李肃当年也见识过魏尚书的案子,牵连的人家不更多?
相比下陈老爷非本案主谋,不过牵涉其中,被人咬住一时脱不开身。
依我看即便南京刑部定案,遇国丧大理寺判决多少要拖后。
陈家当下最多是受拘束,这期间兴许有缓,不至于一竿子打死。
不过,他人事归他人管,咱们自家切不可自乱阵脚。”
他稍思索转过脸道:“三弟寻个机会打点县里和府城,听听他们那边都有些什么消息风声。我去趟省城布政使司托关系。
毕竟孩子们是娃娃亲,当时哪知道后来的事?能用银子遮过去不沾到一点儿腥最好。
不过,这打点是需要银子的,弟妹你看……?”
高二奶奶楞了下,心想果然说到银子了。可她个寡妇家,这样抛头露面的事情少不得靠大伯、小叔帮忙。
想到这里牙关一咬:“他大伯你只管说,这事……要打点多少才好?”
三老爷李严和兄长交换下眼色:“二嫂莫急。我想县尊、府君那里各五百,布政使司那边……最好一千。”
“好,就如此。奴明日让李财送过去!”
李肃见她应得果决,冬瓜脸上浮现出满意神色。忽又想起,嘱咐道:
“哦,还有,陈家大小姐惶急下来家虽情有可原,但避到这里既不方便,也不应该。
临到事头送女成亲,急吼吼明日便要拜堂,亏陈家大娘子想得出!
这事不可操之过急。五郎与大姐儿毕竟还未成亲,相处一院多有不便,先引她去找个空院落安置。
还有,弟妹要告诉五郎莫去陈家张望,要避嫌!更重要的,你家那猢狲要看好。
他和陈家二丫头感情甚笃,这事情五郎知晓还无所谓,他若知道了,谁知会给大家惹甚麻烦?
二弟当初定下两家的娃娃亲也不同我商议,如今他不在了,倒要我来费心!”他叽叽咕咕唠叨个不住,听得三爷李严都有些不耐烦。
“好、好!”高二奶奶连声答应。
想起自己那个庶长子就头疼,不由得叹气发狠:“那小孽畜,奴叫钱氏好生拘束着,看他敢胡来!”
------------------
二房庶长子名唤李丹,今年刚满十五岁。
生母钱氏是二老爷李穆在庐江任知县时纳的妾。
钱家在当地是有名富商,钱老爷(李丹外祖父)相中这位年轻的知县为人、学识都很不错,故而主动把长女与他结亲。
那会儿商人地位并不算高,家中女儿出于联姻目的与官员做妾是很常见的事。
李丹三岁那年母亲去世,不久后李穆即升迁山东东昌知府。
他赴任前得到上司应允送棺柩回庐江安葬了钱氏,又奉岳父之命继娶了其次女,即今被佣人们暗地称小钱氏的钱姨娘。
李穆将她携到东昌任上,李丹就由她抚养。
不料两人还未来得及再有子嗣,李穆在任上突然去世。
小钱氏护着丈夫的灵柩和财产,带李丹回到故乡,将丈夫的家产(他从做县丞到知府,积累了丰厚的宦囊)如数奉上,因此被家族称道。
虽然她是二爷在任上时纳的,并未来得及归乡拜先人、敬主母茶。但族内盛誉之下高氏也不得不容留她,并同意由她继续抚养李丹。
李丹自小便知“钱姨娘”不是生母,那位是她姐姐。
小钱氏自己也不避讳,她把李丹当亲生般抚养,只为保全姐姐与丈夫唯一的血脉。
李丹每每闯祸或做出匪夷所思之举,高二奶奶便归罪小钱氏,抱怨她教养不力。
小钱氏唯唯而已,实际她清楚高氏不断强调她的权威,打着李丹成年后立即分家,借大伯和小叔力量逼自己交出姐姐嫁妆的主意。
她知道二房主母嫉妒钱家的富裕,早心怀警惕不会让其肆意胡来。
------------------
这会儿李府内宅,“小孽畜”推开窗看看天上。
天水骤落后还是阴云密布,四周昏暗,雨还未下透。
但他等不及了,从大厨房(给下人们备饭食的)后窗户钻出去跳进后院,这里是洒扫和花匠们住的地方。
观察四周无人,他背着手若无其事穿过院子,来到旁边院落。
这院是车夫、轿夫的住处,一侧便是李府的西墙。
他助跑几步,脚尖点地胸中提气,跳起来用左脚在柴房侧墙的凹陷处一蹬,借劲拧腰发力,“蹭”地右脚已踏上墙头。
身形稍晃找到平衡,转身轻轻提气,沿着墙脊跑了二十几步,墙外便是株有年头的栗树。
攀枝过墙,抱着树干跳下地,他来到街角。
四五个正在别人屋檐下躲雨,身上落汤鸡般。
身材干瘦、衣衫破烂的乞丐们见到他忙都站起来。
“来来,人人有份。”那少年说着从鼓鼓囊囊的怀里抓出个麻布包,打开看时却是七八个冷馍。
众乞丐每人接一个,拿了便咬。
为首的年长者不好意思,忙作揖道:“谢公子赏。您别见怪,大伙儿都饿狠了。”
“无妨。”少年抬手摆摆,将包裹重新系好,递过去,手指指天上道:
“老苏,雨又要来了你们赶紧避避吧。这几个带回去给女人、娃娃吃。”
他叹口气:“穿城往南走,白马寺那边就有朝廷赈济的粥场了,到那边就能……。”
“丹哥儿,你怎么在这里,让我好找!”面颊淌血珠的青年从巷口大叫着跑来,用衣袖遮在额头上,气喘吁吁道:“兄弟们遭人欺负了,等你来撑场子呢!”
“杨乙?你这是怎么了?”李丹打量他那惨兮兮的模样吃了一惊。
“城南赵老三那厮不知发什么神经,跑到咱城北来疯。”
杨乙回过气来急急道:“他在春香楼请人吃酒。这也罢了,无端端非要唱曲的幺姐儿陪酒。
姐儿说如今时节不对只能唱个曲,他便要手下拿了人回府,说要替妈妈调教。
苏大娘吓得叫了我们去,谁知兄弟们刚进门那厮便大喊‘动手’。
弟兄们措手不及,我跑来寻你时已经被打伤四五个,张金刚的胳膊都折了……。”
“别说了!”李丹打断他,眼里已经喷出火来,冲到巷口嘴里问:“可有衙门公差到场?”
杨乙忙在后头答:“不曾!”
李丹心中冷笑,捕快们要么是畏惧赵家,要么是得他什么好处远远躲着看动静了。
------------------
看着他背影一名乞丐说了句:“这小哥有意思,又行善、又抱打不平。长老,他们刚才说的该是昭毅将军家的三公子?”
“可不,”苏老头也不抬地吃着:“那小混账今日有人料理了。上次张兄弟被他家狗当街追咬,这个账今日正好还。”
“照您这么说,咱不是又欠了李三郎的情?”有个小乞丐抬头问。
“承情。”老苏叹口气:“可他是李家三郎,咱有什么路子还他呢?诶,只好寻机会喽!”
说完他看看这几个伙伴:“大家记着这事儿,但凡有机会……。咱丐帮不兴欠别人的!”
------------------
余干县城夹在信江和余水间,南北狭长。
城北原有群青皮,号称八虎,互相争地盘不能抱团,曾被南城势力压了多年。
不想两年前冒出这李丹与数名少年结成“七人众”,镇住城北并收拾了南城一顿,名声大噪。
因他身高修长,生有蛮力,又恰姓李,故而被送了个名号“小元霸”(即唐高祖李渊第三子李玄霸,民间讹传其名为李元霸,以勇力著称)。
名号叫响了,城北风气渐变,无人敢做那等欺行霸市、欺男霸女的勾当。
本县西市在城北,主要经营牲畜、首饰、丝绸、棉布、铁器等类。东市在城南,主要经营米粮、食材、调味料、日用、瓷器。
北城因李丹等的维护,环境安定、商业氛围逐渐盛过东市,这让杨乙口中的南城赵老三满是羡慕嫉妒恨。
赵老三官名赵煊,莫看诨名,其实是个皇族末裔的纨绔子弟。
他仗着老爹袭昭毅将军爵位,整日游手好闲,豢养青皮无赖,干些欺男霸女、侵扰商户的坏事。
自被李丹狠狠收拾过,南城气焰顿消,形成了互不相侵的格局。
两边无声地有了规矩,若到对方地面上去须得提前打招呼,免生误会。
赵老三贸然闯入实是无理。
李丹放慢脚步,春香楼已不远处,这才发觉自己两手空空。
抹把额发上滴落的雨水,李丹瞥见酱菜铺门口撑雨蓬的挑棒,伸手抓过一根,叫声:“楚老倌儿,回头赔你!”磕在腿上一撅两截。
那楚老倌儿篷子倒了半边,却吓得缩了脖子半个字也说不出。
李丹将棍子往背后一插,背手迈上台阶。
春香楼原是本城有名的花楼,在李丹扶持下转为高档餐饮,但在外人眼里还是有些夹缠不清。
掌柜(妈妈)苏大娘其实还不到三十岁。按说来此的哥儿都是寻欢作乐的,被砸楼可是头遭。
国丧期间又连遭阴雨生意指定好不了,不想进来几位爷,竟还拿着闹事的主意!
苏大娘转眼见满堂哀嚎、一地鸡毛,吓得花容失色,往日的态度早已不见。
她钗环凌乱,身上的宝色苏绣褙子不知何时被泼上了各色菜汤酒水,显得狼狈至极。
李丹大踏步走来,她便如见到青天大老爷降临般“哇”地哭了出来,叫道:“丹哥儿,你看这好端端的……叫什么事?你可得帮奴家做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