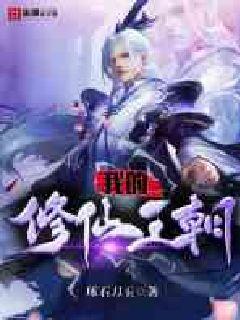襄阳南边的城墙面对荆门腹地,多年以来缺乏修缮,隔年的旧草在坑坑洼洼的缝隙间摇曳,护城河的波动吹来淡淡腥气。
还没等手下人赶到城门上,朱序本人倒是三步并做两步跑了出来。他走到城墙上,居高临下往下看去。天色风云变幻,云气在山中凝结,眼看着又有下雨的意思。
护城河外面站着一个少年,素白的道袍利落第穿在身上,深色披风在他身后随风而动,与其说什么仙风道骨,倒不如飒爽英姿来的贴切。如果有见过的人,便能认出,他身上的乃是太一宗的弟子服。
魏晋以来,世人多尚美,若以美少年的标准去衡量萧慎,则显得过分有棱角,稍差一筹。如果用北方的孔武来要求,又年纪太轻所以纤细。不过他沉着地站在万箭所指的靶心,城上的景象衬托之下,少年人看起来更加气度不凡。
“快收起兵器,打开城门迎接。”朱序下了命令。守在南城门上的两排士兵听了,忙把长矛搁在一旁,几个人都在一起,七手八脚地弯下腰来去解那锁链。
看见眼前的场景,朱序微微一皱眉头,眼皮不详地跳动了一下。累月的鏖战让守城的军士身心俱疲,稍得空隙便抓住机会懈怠,现在连开个城门一般平常的军令,都没划出个你我他之分别。他镇守襄阳不过一年,还没整顿好军纪,刀兵也抵城下,多年的严谨治军恐怕要毁于此处。
“不必了。”萧慎一直关注着上面的动静,听到这句话,朗声说到。随后一手扔出符纸,卷起一阵骤起的风,风力虽然大,但是吹过的范围不过一二丈宽,卷起一地沙尘。一卷风沙过去,他正正好好飘然落在城头,白袍了无纤尘。
虽然曾经见过修仙之人,朱序还是看得目瞪口呆,只觉得不愧是仙家子弟。这一手看似呼风唤雨来的随意,实际上咒符繁杂,威力也有限,他露这一手大半是为了取信于朱序和诸位军士。假如他真的能有移山填海之能,又何必亲自来襄阳城里呢?
萧慎从女墙上轻轻一跳,落在朱序面前,解下腰间流云剑,右手握着柄鞘处,微微一拱手:“朱将军,久仰了。”
“这位郎君这么称呼?”
朱序想回应,但是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叫仙师,显得自己没有见识,又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好称呼。只好选了一个时下比较通用的敬称。
“我叫萧慎,太一宗山人,将军不用拘礼。”他看出来朱序的尴尬,就说了自己的名字。至于如何认得朱太守倒是没有明说,其实一半来自于道听途说,一半是因为那封密信。因为是太一宗底弟子,萧慎也没拘泥于俗世的那些礼节,三言两语就和朱序攀谈起来。
“尊师一向可好?”
朱序不说旁的,只谈仙门和家人。萧慎听得有些急切,他不知道如何才能顺利的取信于太守,让他相信自己带来的消息,只好顺着他便说下去。
“承蒙关照,白鹤峰主是我师叔,现在还在山上修行。”
“哦,这样啊。那萧郎此次下山可是因为有师尊的嘱托?可以暂去府上歇息片刻,和家母叙叙旧。”
“那就多谢将军了。”萧慎虽然没经历过纷争前线,但是绝对不多好奇,一路走来目不斜视,一派镇定。
朱序是很客气的,但是心中难免有些怀疑。此时襄阳城风平浪静,在守城诸位将士看来,似乎是汛期将至,北军想要退缩一二十里地,据守对岸樊城的样子。连他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便令全军暂且修整一段时日,不再谨防死守。
可是在萧慎眼中,隐隐有着风暴降临的先兆。他出于一点意气,情急之下投奔襄阳,眼下却不知如何开口才对,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紧锣密鼓。
走着走着到了太守府门口。
应该找一个理由和他说起密信的事情,萧慎顺着话题讲下去,一遍暗想着,开口说道:“将军如此警惕,也是对萧某此行意外吧。”
朱序被萧慎点破,就坦然承认:“贵宗仙人向来隐居云端,不想两军交战之时却见到。”
“如果我说,萧慎此行三分是拜访老夫人,七分是为见太守,将军会不会惊讶?”
正穿过大门,朱序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萧慎。门楼之上风声呼啸,他一身黯淡银铠不为之动摇。毛遂自荐之人,他见得多了。自从八王之乱以来,天下士人纷纷寻找投奔好去处的机会。现在固守襄阳的一派军师武将,也都是来来往往中留下来的。所以他马上答到:
“不惊讶,但是萧郞的确是仙宗门下,让某一时难辨真假。”
“朱将军也说了,想投机的人总是不缺的。有多少人自比周文王,就有多少人想当姜子牙。”萧慎依旧笑着,不卑不亢,端正平和。
听到这句话,朱序敷衍闲谈的态度开始变得认真,脸上浮现出思考的神色。
作为曾经投身桓温军中,半生戎马的征虏将军,朱序对于这些仙呀道呀的了解实在不多,也并不知道白鹤峰主是谁。但是有一点他知道,如果仙家人出现在两军交战的前线,恐怕意味着这一方多出了不为人知的杀手锏。
朱序此人,有时经常想得不够远,比如之前对北军渡河竟然不作准备。但是他并不愚钝,经过萧慎一句话点破他便明白了。在萧慎到来之前,襄阳一方并没有什么世外高人支持,却不代表北军之中,就没有隐藏着什么人物。萧慎话中之意,引人深思。
“请。”他一挥手,郑重其事地将萧慎请进了议事厅,而不是原来想去的府后露天庭院。然后示意门口的守卫离开,诺大的厅堂里点着灯,主位后面还挂着荆襄地图,此时却只有两个的。
“先生有什么想说的,不妨直言,朱某洗耳恭听。”
朱序没有坐到主位,反而是隔着案台,端坐在萧慎的对面。他用了求教的语调和称谓,摘下头盔放在身侧,亲手倒了一杯热茶汤。空旷的厅堂和案上油灯的照应下,这位梁州刺史半辈子的沧桑和杀伐都刻在眼角。这双眼睛诚挚而不失威严地看着萧慎,等待他能带来什么生死攸关的消息。
萧慎没有理会氤氲的热雾,一番周转之后他终于得到了能不遮不挡,直接说出了机会,当即说道:
“萧某本没有想来掺杂其中,只是因为追逐一只小妖,路过宜阳城北几十里的地方,见到一个古怪的人。”他隔空在地图上圈点了一下。朱序眯起眼睛,宜阳在汉水南下的下游,对于襄阳战场来说,已经属于不近的后方。
萧慎却不再看着他的神色变化,飞快地讲下去。
“那人是凌……也是修士,遮着脸。他驱使小妖送信,信从城里递出,里面提到有人私通北军,想要打开城门相迎。”
“信中可有署名?”朱序问,紧看着地图上的山川河流,布防旗标。
萧慎摇摇头:
“有署名,但是字迹不清。只说某沛,不过提头是写给长乐公。”
“符丕。”朱序接道,恍然大悟,起身拱手施礼,说道:“多谢先生。”
萧慎没有回,只是稍稍避开,说:“将军还是快些查清,严密看守。”
朱序刚想出门,刚掀开帘子,忽然回头问:
“那……那位修士,先生。”
“打不过。”萧慎知道他想问什么。朱序脸上并没有表现出失望,不过萧慎猜想他多半此时心中已经没有底了。
若说为大义而来,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半还是托词。萧慎无论如何都会来襄阳的,韩夫人是玄素真人的亲姐妹,玄素道君襄阳围城即将并不知情,又早早脱离了世俗,从未要下山的弟子帮自家什么忙。但是既然萧慎碰巧遇到了师叔的亲眷,他作为太一宗弟子,于情于理都要加关照三分,遑论是在危急关头的战场上。
确保平安无事,他就可以找到机会离开是非之地,继续他的云游。此时的萧慎万万没想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稍晚一些的时候,萧慎前去拜访韩老夫人。却被告知老夫人在西北巡城。萧慎跑过去一看,韩老夫人虽然年纪不轻,两鬓银杯还手持拐杖,走起路来却大步流星、脚底生风,一副大将出巡的样子。至于那副拐杖,恐怕还能用来打人。
见到萧慎,韩老夫人露出来看着可心后辈的那种笑容,朝他走过来。
“这位郎君,就是我那妹妹的徒弟吗?”
看见老夫人走下台阶,萧慎连忙去扶。谁知道她眼睛一瞪,横眉冷对的气势驱走了萧慎和身边的婢女。他讪讪一笑,只能在一边看着。
“玄素真人确实是我的一位先生。”
老夫人点点头,若有所思:
“这么说,她也是仙道有成了。”
“真人自然是德高望重。”萧慎笑答。韩老夫人同萧慎一道回府,期间又问此来何事等诸多问题,萧慎都一一回答。说道那封密信的内容时,韩老夫人忽然抓住身旁婢子的手:
“前几天因为城上纵马被责罚的,不是一个叫李沛的吗?他不是李督护的儿子吗”
婢女愣了一下,回答道:“回夫人,是这样。”
韩老夫人一个翻身跨出门外,萧慎拦都拦不住,她叫来门口的守卫:“快叫你们将军来!不对,先去抓李沛!”
萧慎劝她回到屋子里之后,这位脾气不小的韩老夫人依然恨恨地骂道:
“李伯护小人!”
不多久一阵骚乱,朱序挎着剑一大步踏入府中,脸上掩饰不了的充满疲惫,衣袍上似乎还有血迹。
“李沛已死,但是李伯护此人,却不知所踪,我已经命令全城戒严,今夜还是多加小心,但是……”
朱序看着自己发母亲,言又欲止,最后只是悄悄的用眼神示意萧慎。萧慎会意,跟随朱序来到廊下,朱序看着禁闭的窗户,忧心忡忡地说:
“秦军三路兵马,十倍于我守军。不用里应外合,也能够耗死襄阳。上明桓豫州将军拥兵七万,援军却……”
说到一半,朱序忽然叹了一口气,停住了。驻守荆州的桓冲名门世家、累立战功,也不是他能够说道的。
“我只求一件事情,先生是仙门弟子,符丕断然不会为难。如果襄阳失陷,还请先生帮助家母出城。韩氏仆婢皆怀武功,只要出城就可以互送家母,避难老家鄱阳。”
萧慎未曾想到自己匆匆而来,还是没能帮朱序揭开困顿,眉头微皱,问道:“将军纵然先得了消息,也无险可守吗?”
“连日不防,敌我悬殊,援军不至,如何能赢?”
“还请将军因地制宜。”
夜已经深了,朱序沉默不语,半晌,点了点头。
忽然夜中一片喊杀声传来。朱序披挂未卸去,当即出门登城。
“我军能赢吗?”
韩老夫人夜不能眠,坐在藤椅上假寐,听到躁动便住着拐杖其身,一个婢女给她打开帘子,老夫人看到萧慎,问道:
“太守已经先说了要输。”
萧慎无奈地说,跨出太守府的门,仰头只见城头东北门火光冲天。再登上高楼望去,火光照应着漆黑河水,成千上百的船板满载秦兵抢渡而来,而原本紧闭着的城门,已经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