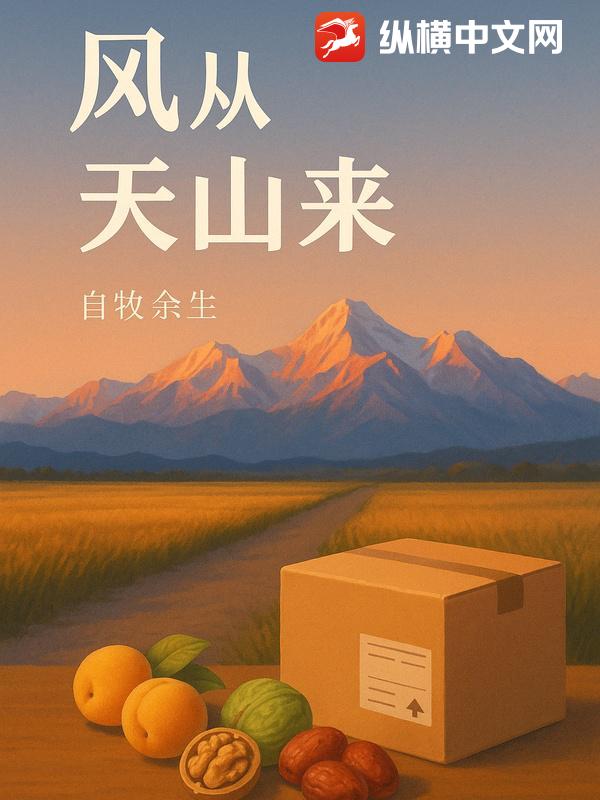夜里凉下来得慢,院子里的热气贴着地面往上冒。苏蔓把电脑合上,抬头看了一眼白板,嘴里嘟囔:“今天这几条,明天都要挂公示栏。”古丽嗯了一声,把记号笔往旁边一插:“你先去歇会儿,我把最后一张表填完。”
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桌角那叠单子吹动了一下。老热合曼端着茶走出来,坐在台阶上:“今晚不折腾了,逐条写清楚,明天一早我再抄一次,写得大点,别让人眯着眼看。”他抬手往门外指了指,“巴扎那头又有人背地里说咱们‘吃得太多’,到时候还得你们俩站出来说个明白。”
“让他们来看账就行。”古丽把笔帽扣上,语气平平,“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写在板上,贴在墙上。能说通的就说,不能说通的也别掰扯。”
苏蔓想了想,低声道:“别生气啊古丽姐,我就是觉得有些话必须说,早点说,比拖着强。”
“我不生气。”古丽笑了一下,“不就是把话说明白嘛,咱们又没欠谁的。”
屋里灯光把院子照成一小块温暖的黄。远处传来买买提江的车声,稳稳的,没有多余的动静。
县城的住处里,李明把手机亮度调低,重新看了一遍今天的留言。他今天在课堂上没讲几句“高屋建瓴”的话,多半是把他们院子里跑通的小事一件件摆出来——什么地方要提前说清,什么地方要当场拍照,哪一句留在公示栏,哪一句写在承诺卡上。
台下听的人有学电商的,也有半路出家的年轻人。问得最多的不是“怎么爆”,而是“怎么不乱”。
课散了,有人非要拉他去夜市吃烤肉,他婉拒了。手机震了一下,是古丽发来的照片:公示栏右上角,多了一列“这周改动”,标注得干干净净。下面还有一条语音——
“明天不做‘说明会’,不摆讲台。就把桌子搬出去,谁有话就站到桌前说。能拿数的拿数,能拿图的拿图。胡老板说要来,他要当面问问,我们就当面答。”
李明回了两个字:“稳着。”
他又想了片刻,多补了句:“别针尖对麦芒,先把‘怎么收’‘怎么算’写得清清楚楚。至于外头的闲话,咱们只说事实。”
手机屏幕暗下去,窗外有风掠过。他把手边那页纸又摁一摁,上面写着几行大字:“人先稳,事再推进。”
第二天傍晚,院口摆出两张长桌,桌上压着铁夹子和几摞纸。白板立在门边,老热合曼用粗笔写了标题——“这一个月,我们做了啥”。
人来了,不闹,先围着公示栏看。苏蔓把昨天整理的“结果、问题、怎么改”三栏依顺序贴上去:“时效多少、坏件多少、怎么赔付、谁跟谁打了电话、哪天的照片。”字不多,都是关节处的实话。
胡老板穿了件旧牛仔服,手里拎着一袋核桃。他把袋口往桌上一放,不坐,开口也不绕弯:“我就问一件事——你们线上走得快,线下还让不让人活?你们说不截我货,我信。可总有人来巴扎上问,说‘线上价’多少多少,拿这个压我。我是不是得以后的都往你们院里送?”
古丽点点头:“您先听我说两个事。第一,线上挂的是标准件,分级、分袋、贴标,出了问题我们兜着。线下你按行市收,收散货,快,有活路,这是两条路。不直接比。第二,谁拿‘线上价’压你,你就指公示栏:标准件什么样,散货什么样,明明白白。我们也不会跑巴扎上去喊价。边界我们守着,不挡你路。”
胡老板没坐,眼睛却软了些:“行,我回头就这么说。”
刚说到这儿,阿衣丁在人群里举了举手:“我说一句,我这个月在这边送了十几趟,规矩越来越清楚。唛头贴歪了当场撕,核桃有潮味当场退。我以前在巴扎摆摊,嘴笨,说两句就打结。现在我懂了,话不多,就拿出来给人看——‘这张图,这是检视编号;这个码,对应这箱谁验的。’别人就不吵了。”
院里一阵轻笑。有人接着问:“那售后呢?有人收货不高兴,咋办?”
苏蔓把手一摊:“手续就三步:给照片、说问题、选补偿。我们这边看图说话,不跟人抬杠。真正糟心的,一月也没几件,能解就解,解不了咱也认。”她顿了顿,补了一句,“但前面说清,后面就少闹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有人问:“日后要扩,怎么扩?”
古丽看了眼白板:“我们不一口吃成胖子。邻村要来,我们先挑一个条件接近的,照搬一遍,合不合适调一调。我们手里几个人,能力就这点,不虚。”
“那你说的‘不乱’,可有个法子?”胡老板又开口。
老热合曼咳了一声,笑:“法子不多,写板上,贴墙上,照着来。咱们是做事的人,不是说书人。”
一圈话说下来,院里不是喊口号的热闹,是一种顺气的松。有人把随身带着的小本子翻开,又有人干脆举起手机拍。说完就散,没有鼓掌,也没有谁站出来再拔高一段。天色往暗里去,门口风把旗子轻轻吹起一点角。
那天夜里,李明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自己是省城的批发商,口气爽利:“看你们那套做事还挺规矩,我手里有个商超渠道想试一下。但我要量价都稳定,你们能不能每周给我固定几吨?”
李明没急着答,随手把窗帘拉开,街上灯火一点点。
他声音放缓:“哥,先不谈几吨不几吨。我们这边的活,靠的是老乡一筐一筐交上来的规矩。你要稳定,我得先看看你要的‘稳定’是什么意思——稳定的规格,还是稳定的数量?这两个不是一回事。数量我现在不敢拍胸脯,规格我可以给你看我们这一个月的表。你要是想着一步跨两级,那我只能跟你说‘慢点’,免得一脚踩空,摔了老乡。”
那头沉默几秒,笑了一声:“行,你这话,说得我消气。你把表发我邮箱。量咱慢慢谈。”
李明挂了电话,给古丽发信息:“有个外头的大客户来按门铃,要稳住,不要冒进。”
古丽回:“知道。院里这头,我们守着。”
李明靠回椅背,脑子里浮出院里那张公示栏,贴着“这周改动”的红框。他写下一行字:“外头伸手,我们把握节奏——要人、要规矩、要底线。”
第二天上午,风沙没起,日头倒是正。古丽进县里一趟,把上次用坏的糖度计送去修。
回来的车上她没睡,一路抱着个硬壳文件夹,里面夹着最近几次“公开账本”的图片和笔记。她把夹子边缘抹平,像抹一块玻璃。
下车的时候,苏蔓在院里招呼她:“姐,这两天我想做一个人——咱不拍货,就拍人。拍谁呢?我想拍胡老板。”
古丽愣了一下,笑道:“你这心思,比我细。”
“他不是心里有疙瘩么?你我再怎么说,他只当是‘官方的说法’。”
苏蔓挠挠头,“让他自己讲,讲他怎么收货,讲他怎么讨价还价,讲他也被人压价的难。大家看了,也就知道线上线下不一样。”
古丽想了想:“行。别给人硬安排,要不真成摆拍了。”
当天傍晚,两人去巴扎。胡老板正蹲在摊前,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削核桃皮。
苏蔓没上来就拍,先蹲在侧面等了一会儿。等胡老板一个客人送走,又过了一个,才开口:“胡叔,拍你两分钟,行不行?不问价,不打岔,你就照着平时说话,怎么来怎么说。”
胡老板抬眼看她们,想笑又忍住了:“你们这俩,嘴甜得很,还会选时候。拍就拍,不要在我旺的时候挡人。”
镜头开着,胡老板把刀放下:“我就干这一行,二十多年。眼睛不算毒,耳朵还行,听人说话就知道想法。不管线上还是线下,东西归东西,人归人。你把人说顺了,东西自然好说。有人拿‘线上价’压我,我不跟他吵,指指这堆货——‘你是要标准件,还是要这堆散货?’说清楚了,也就散了。”
两分钟不到,苏蔓收了镜头。走回院子路上,她对古丽说:“人是通的。话说清了,事情就顺了。”
古丽点头,没说话。
县里这边,李明连续给三个乡镇讲了“把账摊开”的办法。
有人起头问:“你们咋就不怕别人抄?”李明摆摆手:“抄不抄无所谓。咱们做事不是靠‘秘方’,是靠一条一条站得住的规矩。抄去就抄去,只要按规矩做,抄也能过日子;不按规矩做,抄来抄去也会乱。”
下课后,有个年轻人追出来:“李哥,我说句实在话,我最怕的不是做不来,是镇上有人说‘你们这帮年轻人只会整花活’,一句话就把我压回去了。”
李明没安慰他,只拍了一下他的肩:“你就把东西摆在他面前,摆三回、五回、十回。你自己不走,他怎么挤你都没用。记住——‘不跟人吵,跟事较真。’你要是真想做事,这句够你用很久了。”
那年轻人笑了一下,点头走了。
李明站在教学楼长廊,给买买提江发消息:“你帮我留意一下吐尔逊那边的柜,最近电稳不稳。我们手里有备用的发电机,但别真指望它。”
买买提江回得快:“放心,我晚上路过就看一眼,吐尔逊也熟了,照咱们的条条做。”
李明把手机收起来。光线从走廊尽头涌出来,他突然想起一件事——秋后。
核桃要收尾,枣干要稳。他心里盘算着:秋后,能不能拉一条“人”的线——把院子里这套“公开账本”的人手扩大,拉几个愿意讲、讲得明白的年轻人,去邻村跑一圈。
办法不求多,一村只留三条规矩:不瞒、不乱、不拖。其他的,慢慢叠。
他把这三条写进本子:“秋后,人要扩,规矩不动。”
院子里,晚上没开会,大家各做各的事。苏蔓把“胡老板两分钟”剪成短视频,没加花哨的字,就加了个标题:“一辈子收货的人,怎么讲价。”
古丽在白板上写下一列新字:“下周:邻村试点——先看人;院里沉淀——轮换值守;外头来客——不许许诺。”
她把粗笔放下,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转身进了屋。
老热合曼在门口拆了个插线板,又用胶布把线捆得整整齐齐。他抬头看见苏蔓,笑:“你们年轻人有劲儿,有愿望就能成事。我年纪大了,手还算稳,能把线理顺,也算帮着你们。”
“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大脑。”苏蔓故意逗他。老热合曼摆摆手:“脑子不敢当,能记住电闸在哪,也就不算给你们添乱。”
两人正说着话,胡老板从门外探进头:“我刚才那段,别给我剪得太漂亮,免得别人说我装。”
“放心,原汁原味。”苏蔓笑,“你就把今天这一句留给我——‘人说顺了,事就顺了’。”
胡老板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古丽看着他的背影,轻声说:“他心里那点疙瘩,往外拔了半截。”
深夜,院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古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很久睡不着。她忽然想到父亲前几天打的那个电话:“姑娘,别太累了。你在镜头里说话,我看着觉得你还是个小孩。”
她在被窝里回了一条长长的语音,没发出去。又删了,换成一句短的:“爸,我没丢人。”
发出去以后,她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枕边。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点干燥的草气,很轻。
天快亮的时候,李明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站在院门口,白板上一行新字:“人走到哪,规矩跟到哪。”他伸手去摸,指尖碰到的却是一层薄薄的水汽。
梦醒时他笑了一下,翻身坐起来,拿笔把那句梦里的字写在本子上,写完又画了个小框。
窗外的城市刚亮,远处的楼顶是一刀平的灰白。李明把背挺直,对自己说了一句:“回去吧。”
他不是要立刻回去——还有最后两天课要结。但那句“回去吧”,像是对着心里那盏灯说的。院里的灯,城里的窗,两处都亮着。一条线从心里穿过去,把人拉成一块。
这天傍晚,短视频发出去,评论不多,但每一条都像是真话:
“我们这儿也是,卖货容易,说话难。看完懂了。”
“胡叔这句话真好,‘人说顺了,事就顺了’。”
“能不能把你们的‘公开账本’拍一拍,给我们看看怎么写?”
苏蔓把这些评论念给古丽听,古丽没笑,只说了句:“那咱们就拍,别打光,别摆拍,就拍墙。”
她又补了一句,“把李明的那三条也拍进去——‘不瞒、不乱、不拖’。”
“好。”苏蔓点头,抬起手机对着公示栏,把镜头往上一推,停在那三条前。光在墙上轻轻铺开,字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影子。
夜越深,风越轻。院里的灯灭了,城里的窗也一盏盏暗下去。谁也没说“路有多难”,谁也没说“明天有多顺”。大家只是把手里的那点事做好,把该贴的字贴好,把该说的话说清楚。
人心稳住,风过也不乱。
下一步,往外走,但脚下不乱。
这话没人写出来,却在每个人的心里头,像一条细线,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