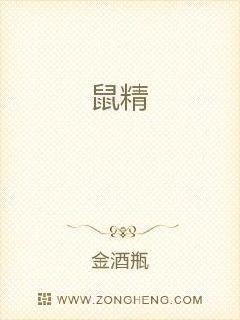这是一个春天的晚上,星期天。广场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春风惹得满身香气,像平静的湖面的微波一样在广场上荡漾。广场的中心有一个音乐喷泉,在下面一排五彩缤纷的灯光照耀下,伴随着贝多芬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喷泉变幻着各种各样的造型。
“孔雀开屏!……天女散花!……啊啊啊!水上芭蕾……” 一个笑靥如鲜花的女孩拍着巴掌欢叫着,声音清脆悦耳。她有二十来岁,高挑个子,穿着风衣,名字叫景爽;她身边那位戴着眼镜、瘦高个子的男青年是她的男朋友艾嘶鸣。
各种炫丽美妙的造型在高空昙花一现,旋即跌落下来,哗的一下,摔成一片碎珠烂玉。艾嘶鸣仰着脸瞧着,眼睛里闪着光辉,忽而目光又黯淡下来,低下头轻轻叹了一口气,幽幽地道:“美丽凋谢得这样快……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长久的呢……”
“你啊,又在抒发诗人的忧伤……” 景爽挽着艾嘶鸣的胳膊,用身体轻轻碰了他一下。“这世界上当然有永恒的东西,比如咱们的爱情……” 她用炽热的目光融化着艾嘶鸣眼睛里的忧伤。两人的手十指交扣,紧紧握在一起。
广场上的人很多,很热闹,有跳广场舞的,有孩子们的玩闹,有说笑聊天的,有情侣的耳鬓厮磨。但是只要景爽和艾嘶鸣互相依偎着从人们身边走过,大家的目光都会被吸引过去,因为景爽太美丽了,男朋友太有气质了,真是一对神仙情侣!有穿学生服的女孩悄悄告诉她的家长:两人都是我们县一中的老师,男的教语文,女的教英语;他们是恋人,还没结婚。
时间不早了,景爽和艾嘶鸣挽着胳膊从广场上出来,回他们住的公寓。路灯黯淡,路边是一片黑魆魆的烂尾楼,忽然从路边被荒草湮没的下水道里窜出一只老鼠,前爪抓着景爽的裤腿,在她的脚边直立着,吱吱吱直叫唤。
艾嘶鸣低头定睛一瞧,又惊又怒,一条腿往后一抬,就要飞起一脚,把这只可恶的小畜生踢到几十米外烂尾楼的乱草丛中。
“且慢!” 景爽忙伸手拦住他,“这不是老鼠,是仓鼠!你看,它是没尾巴的……”其实她不知道,这是一只成精的老鼠,自己咬掉自己的长尾巴,冒充仓鼠,邀人宠爱!景爽蹲下来,小心地把鼠精捧到手里,仔细端详着。这只灰色的小东西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惊恐地转动两只黑溜溜的小眼睛。“这是谁家的仓鼠跑丢了?还是遗弃不要了……你瞧,它多可怜啊!”她把鼠精放到掌心,另一只手不住地从上到下轻轻抚摸它的皮毛,就像抚慰一只小鸟。
不错,这个小东西确实没有尾巴,但是,除了没有尾巴,和老鼠有什么不同……艾嘶鸣不懂仓鼠,从心眼里不待见它。
“我要把它带到家里,养起来!” 景爽说。
艾嘶鸣知道景爽素来 喜欢小动物,没吭声,算是默许了。
第二天,景爽为“仓鼠”买了一个小笼子,小笼子里还有一个小房子,很豪华。“仓鼠”很兴奋,一会钻到小房子里,一会在笼子里攀来爬去,吱吱吱地欢叫不已。景爽发现“仓鼠”非常贪吃,每次喂食,它都要把肚子吃得像一个滚圆的小球球,躺在笼子里不能动弹。景爽觉得又好笑又好玩,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贪贪”。
小贪贪很淘气,神出鬼没,喜欢玩失踪。那天放学后,景爽回到家里,看到笼子里——每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她总要先逗逗小贪贪,喂它吃东西——空空如也,一下慌了!笼子的缝隙很小,它不可能钻出来啊……啊!一定是谁把贪贪偷走了。但是门窗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小偷进来也断然不会偷一只仓鼠……真是活见鬼,小贪贪到哪里去了呢……“小贪贪!小贪贪!!你在哪里,出来啊……”她在沙发底下、床底下乱找,翻箱倒柜乱翻。“吱吱吱!”景爽忽然听到贪贪的叫声,声音好像是从自己身上发出的,她在自己身上乱摸乱找,发现贪贪竟然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探出头来!景爽把贪贪放到自己的掌心里,轻轻在它身上拍了一下,“你怎么钻到我的口袋里了……我还以为你跑丢了呢,吓死我了!”
原来,这只鼠精有神奇的魔法,它能在 景爽光洁的皮肤上突然消失,像一滴水渗入到土壤里,它发现景爽的心房才是最舒适的栖息地,远比笼子里的小房子舒适。同样的道理,贪贪也可以凭空在景爽的身上现身。 它有时在小笼子玩耍、睡大觉,有时钻到景爽的口袋里、包包里。时间长了,景爽就习惯了贪贪的神秘莫测,笼子里看不到它也不会急得到处乱找,知道它不是在自己的口袋里就是在自己的包包里,甚至是与自己融为一体了。
然而,艾嘶鸣始终很嫌弃贪贪,说它身上有一股臭气。“没有!我在它身上撒了香水呢。” 景爽反驳道,翻起大眼睛瞅了艾嘶鸣一眼,撅起小嘴巴。她认为艾嘶鸣不喜欢小动物,满怀成见。
艾嘶鸣和景爽五一节就要结婚了,他买了一套房子,也装修好了,这天带着景爽去看新房。景爽到各个房间都转了一下,看到房子的装修都很简单。她又来到阳台上,往下一看,不禁伸了一下舌头,地上的小汽车小得像甲壳虫,人像蚂蚁。这是二十一楼,最顶层。顶层容易漏雨,房顶隔热效果也不好,只是有一点,房价便宜点。
现在的房价很贵,顶层的房子一平方六千多元,房价加房贷利息共一百多万。艾嘶鸣的父母都是农民,倾其所有帮助儿子买房子,他们住的还是低矮的老房子,房子漏雨,房顶上盖着塑料布。但是老两口提起儿子儿媳 都是满脸的自豪和幸福,两人都有体面的工作,儿媳又是万里挑一的。一想起父母,艾嘶鸣就会眼含热泪。
“我们是离天庭最近的人,夜里能听到星星私语,听它们唱歌……” 艾嘶鸣一只手搭在景爽的肩上,眼睛里闪着光辉。
“ ‘ 子是清溪鱼,食水得安逸。’ ”景爽把脸贴在艾嘶鸣的胸前,幽幽地说。
“我会努力工作的,多挣着钱,不会让你,还有咱们未来的宝贝跟着我喝西北风的。我现在是班主任,每月有班主任补助,业余时间我还干家教……” 艾嘶鸣忙说道,一面用手抚摸着景爽的后背。
景爽把脸埋在艾嘶鸣的胸脯上,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没吭声。一个月多挣仨核桃俩枣的,会到哪里去……艾嘶鸣每月交房贷三千多,要交二十年,当房奴啥时候是个头啊……
贪贪从景爽的身上下来,拉屎撒尿,又迅速回到景爽的口袋里,仿佛屋里的空气有毒似的。
自从景爽养了贪贪,她们家就没有安生过,今天这被咬坏了明天那被咬烂了。这不,贪贪这天就闯了大祸!
这天下午从学校下班回到家里,景爽到厨房做饭,艾嘶鸣来到书桌前面,坐到椅子上,很舒服地舒了一口气。当老师忙,当班主任尤其忙,事多事杂,他心里又有了作诗的灵感,要创作一首诗,也好让心灵得到一种休息。
“该死!该死!!贪贪!我要宰你,宰了你……”
外面忽然传来艾嘶鸣的怒骂声,还有“嘭嘭嘭”用拳头捶桌子的声音!景爽吃了一惊,外面发生了什么,贪贪又干坏事了吗……艾嘶鸣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不大声说话,从不发脾气,今天是怎么了……她丢下饭锅,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只见艾嘶鸣直挺挺坐在那里,面如金纸。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从书桌下面抽出来的抽屉,抽屉里满满的都是噬咬成的碎纸屑,夹杂着密密麻麻大米粒大小黑色老鼠屎,纸屑上有片片淡黄的干尿渍。抽屉里原本放着两大本厚厚的诗稿,基本上都是艾嘶鸣大学四年里写的,包括写给景爽的三、四十首爱情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开发表过的;还有一本艾嘶鸣极其钟爱的普希金爱情诗集,因为时间太久了,他又经常翻阅,显得很旧很破。这些宝贝可比艾嘶鸣的命还重要……贪贪啊贪贪,你淘气也就罢了,可是你干点什么不行,竟然敢钻到艾嘶鸣的抽屉里——这里可是他的圣地啊——肆意毁坏玷污……你、你闯下大祸了啊!
贪贪躲在笼子里的小房子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向外窥视着。
“嘶鸣!嘶鸣……你消消气,消消气啊……”景爽摇晃着艾嘶鸣的肩膀,焦灼地呼唤着。“都怪我不好,非要养一只仓鼠,惹你生气了……咱不养它了,明天就把贪贪送人,好吗?”景爽啜泣着说。
艾嘶鸣两眼含泪,嘴唇哆嗦着,说:“我写给你的几十首爱情诗,没有了……贪贪,它……它噬咬了我们的爱情……”
“我不是在你身边吗,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景爽依偎着他说。
艾嘶鸣抚摸着景爽放在他肩膀上的手,喃喃地说:“我看到那些有些泛黄的稿纸,看到写给你的诗,看到当时的笔迹,看到诗的写作背景介绍,看到下面缀的日期,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大学时代,重新体验咱们美妙的热恋……可是现在,没有了那些诗稿的引导,我回不去了啊……”他说着哇地哭了起来,像孩子一样,哭得很伤感!
景爽把艾嘶鸣紧紧地搂在怀里,她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珍珠,纷纷滚落下来。在大学里和艾嘶鸣那一段美好、纯洁的爱情,又闪现在景爽的脑海里。
在大学里,景爽堪称校花,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她的眼光太高,不是嫌这个志趣不高雅,就是认为那个谈吐太俗气。那个时候,艾嘶鸣在学校里已经小有名气,不时有诗作在校报上,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景爽很喜欢艾嘶鸣的作品,不但要反复阅读欣赏,还要剪下来贴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景爽尤其喜欢艾嘶鸣的爱情诗,觉得他的爱情诗像春雷,想春风,唤醒了她内心沉睡的大地,焕发出爱情的勃勃生机;读他的爱情诗,又像和心仪的白马王子骑着天马,在铺满白云的天空自由翱翔;她也认识到爱情原来是火,是海,是生生死死……但是景爽并不认识艾嘶鸣,她非常渴望认识他,常常在心里猜测、描绘艾嘶鸣的样子。景爽喜欢朗诵,参加了学校的诗歌朗诵社团,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终于见到了艾嘶鸣。那次景爽在台上一连朗诵了几首艾嘶鸣的爱情诗,声音清脆婉转,抑扬顿挫,或激情奔放,或纯洁无瑕,或深沉似海,或幽怨低徊……艾嘶鸣没有想到这个女孩能把他的爱情诗的情感表达得如此到位,她还长得这么好看;更让他感动的是,有一首小诗是很久以前发表的,很青涩,她都能背出来……景爽朗诵完毕,台下掌声雷动!艾嘶鸣冲到台上,献上一束鲜花,紧紧握着她的手致谢,作自我介绍。啊!眼前的就是艾嘶鸣吗?高高的个子,有些瘦弱,戴着眼镜,眼睛里闪耀着光辉,这双眼睛就是一首爱情诗,那样炽烈,那样清纯,那样深沉……景爽怦然心动,难以自持,她紧紧握着艾嘶鸣的手,生怕眼前的一切只是幻象,是一场梦,她一眨眼,或者一松手,艾嘶鸣就消失了,眼前只是一场空……就这样,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热恋。毕业后,景爽远离父母,义无反顾地跟着艾嘶鸣回到他的家乡。
此时此刻,景爽也很想回到大学时代,和艾嘶鸣坐在学校操场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谈爱情,谈理想……
“呀!饭糊了……”厨房里冒出浓重的焦糊味儿,景爽赶紧往厨房里跑去。
第二天,景爽也没有将贪贪送人,依旧继续养着,只不过对贪贪管束得严了些。
景爽也在努力地挣钱,业余时间也搞家教。请景爽做家教的可不是一般人,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全县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名字叫金大力,他出的是大价钱,让景爽给他的儿子金山补习英语,劳斯莱斯管接管送。金山是艾嘶鸣的学生,他最差的是数学,英语成绩在全班排前几名。艾嘶鸣觉得金山父亲的做法匪夷所思,太荒唐了,应该让金山集中精力补习数学嘛,补什么英语?!
和金大力接触了一段时间,景爽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被彻底颠覆了,大开眼界,瞧人家金老板吃的用的穿的住的,瞧人家开的车,再看看自己和艾嘶鸣的生活,就太简单太寒素了,何止是天壤之别!金老板日进斗金,一天的收入抵得上她和艾嘶鸣干几十年、干一辈子……在金大力面前,景爽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金大力说话时她总是看着脸色,笑容也有一些谄媚的意思。金大力对景爽更是喜爱有加,常请她吃饭,送她小礼物。
有一次,金大力又开着劳斯莱斯接景爽,他一边开车一边拿出一个包包,递到景爽手里,“你给金山补课辛苦了,哥给你买了一个包包。”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子,圆滚滚的大肚子,没脖子,西瓜一样的大脑袋直接坐在肩膀上,留着茶壶盖一样的短平头,手指甲又厚又长,里面藏着黑色的陈年老泥。金大力原先是泥水匠,是村里盖房班的头,后来到房地产开发工地当包工头,最后成为房地产开发商,越做越大。
包包是粉红色的,绿宝石镶边,摸上去温润舒适,柔软而有骨感,景爽只看了一眼包包的牌子,便像被火炭烧到了,忙把包包还给金大力,连声说:“不行不行!这包包太贵了,我不能要……”这是法国产的名牌包包,网上价格一万多元。
“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你不要给谁?……这包包的颜色太艳,只能你们女孩用,你嫂子的年龄太大了……拿着拿着,别让哥生气!”金大力又把包包塞给景爽。“哥的身家过亿,这点小钱,在哥手里算啥?!”
“那……就谢谢金哥了!”景爽只得收下包包了。也是,一个包包,再贵,在金大力眼里也不值一提!她笑眯眯地抚摸着包包,感叹道:“妈呀!一个包包一万多元,一万多元,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这也太奢侈了吧!”
“哈哈哈哈!一个包包一条皮带之类的小东西,算什么奢侈?!”金大力开怀大笑。“也是,你和艾嘶鸣每月拿那么点死工资,能见过啥世面,会吃过什么喝过什么……哥给你说,景爽,人这一辈子很短,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千万别亏待自己……等你有空了,哥带你到一个地方,让你看看啥是奢侈,尝尝奢侈是啥滋味……”
“那是啥地方啊……”景爽很好奇,绕有兴趣地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金大力挤挤眼睛,神秘地说。
在景爽面前,金大力从不食言,不久后的一天,景爽真的被他带到一个奢侈的王国、人间的天堂!在一个最繁华的大都市,有一个百星级的帝都宾馆,帝都宾馆有一个帝王套间,景爽竟然被金大力带到了这个凡人不敢企及的地方。
帝王套间的女服务员都是宫女打扮,领班是男的,扮作太监,拿着蝇拂,说话捏着嗓子学娘娘腔。一进帝王套间,先由宫女用步辇抬着去沐浴,沐浴后更衣,男的穿上龙袍,女的戴上凤冠,着皇后服,坐到龙椅凤椅上,太监领着宫女们在下面三跪九拜,山呼皇上娘娘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为登基仪式。
帝王套间的客厅像一个篮球场那样大,金碧辉煌,墙壁、天花板都是金黄色的,沙发桌子也是金色的,在灯光的照射下,满屋金灿灿的晃眼!
景爽由两个宫女掺着,身体略一动弹,头上身上的金银首饰叮叮当当乱响,清脆悦耳;脚下的地毯很厚,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
“哎哟哟!我咋不会走路了,头重脚轻,像腾云驾雾……”景爽眯着眼睛,在宫女的搀扶下,像在风中摆动的娇弱的柳枝,东摇西晃。“我咋这么迷呢,脑子里混混沌沌一片空白,哪里是南,哪里是北……我是谁,叫什么,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哦哦!通通记不起来了……难道我喝醉了吗?没有啊,这还没吃饭呢……”她目光迷离,色如桃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惊呼连连。
搀扶景爽的两个宫女都抿嘴笑了,来这里入住的大款带来的年轻女孩大都是小家碧玉,没见过什么世面,都是这幅德性。“娘娘!娘娘!小心脚下,别摔倒了……”她们陪着小心连声向景爽说。
“哈哈哈哈!”金大力瞧着景爽,纵情大笑,吹圆的气球一样的胖脸上红光满面。“把啥都忘光了好啊,和所有的一切说拜拜!你现在是在醉里梦中,美不美?好好享受吧!哈哈哈哈!”穿着龙袍的金大力挺胸凸肚,嗓门又响亮又爽朗。
宫女退到一边,景爽挽着金大力的胳膊,金大力带她看墙上挂的一排巨幅照片,都是些曾经在此入住过的大款、明星,还有贫困小国的政要。“你知道吗?这里的空气都是在原始森林里收集来的……现在城市乡村的空气污染太严重,简直不能呼吸了……”金大力向景爽说道,一面说一面皱眉咧嘴摇头,很是嫌弃。
太监带着他们参观了皇上的寝宫和娘娘的寝宫,皇上的龙床很大,是纯金打造的,像一个金灿灿的小房子,娘娘的凤床也是金子做的,只不过要小些。太监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洗手间和抽水马桶。
“用膳的时辰已到,请皇上娘娘到餐厅用御膳!”太监哈着腰说。
“嗯……前面带路!”金大力仰着脸,用鼻音说道。
太监在前面走,宫女们忙拥上前,像护士伺候病人一样掺扶着金大力和景爽去开饭。
妈呀!餐厅好大啊,能容纳几百号人就餐。只有一个大餐桌,长长的足有二十来米,上面摆满了大盘小碟,盆盆坛坛,说不尽的玉盘珍羞山珍海味,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妈呀!这么多菜,就是两头牛也吃不完啊!景爽瞪大眼睛合不拢嘴,看傻了!
离餐桌较远的地方,放着两把椅子,太监请金大力和景爽落座,然后拉长娘娘腔,像唱一样喊道:“奏乐!喂御膳!”
在音乐的伴奏下,一群舞姬挥舞着长袖跳起舞来。又有几十个宫女,每人端着一个小碟子,每个碟子只盛一样菜,量非常非常小,只有一点点,排着长队喂金大力和景爽进食。宫女们大气不敢出,十分肃静,金箸玉盏发出一片圆润悦耳的叮当声,伴随着金大力和景爽吧唧吧唧的咀嚼声。这么多菜,每样尝一点点就吃饱了,但是菜的种类又太多太多了,绝大部分尝也没尝就撤下去了。
用过御膳,宫女们又用步辇将他们抬到大客厅。吃过饭以后,金大力的肚子更大更圆了。他一面用牙签剔牙,一面在沙发上欠起屁股,放了一个又长又响的屁,感到肚子里好受了一点。
“好酒喝多了,放的屁也冲劲十足!”金大力的脸红得像酱盆,笑着说。
景爽玉颜酡红,捂着嘴嗤嗤地直笑。
“俺不认识几个字,没文化……”金大力的脸上露出很惭愧的笑容。“不像艾嘶鸣,那么有学问……听说艾嘶鸣会写诗,是真的吗?”
“他是省诗歌协会的会员,是诗人。”
“嚄!是诗人……”诗人的名头完全把金大力吓住了,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十分渺小,像一粒卑微的灰尘。“他发表一首诗能挣多少钱……”金大力小心翼翼地问,一想到自己要动的是诗人的女朋友,他就不免有些怵,一面问一面端起茶杯慢慢啜了一口茶。
“几十块,一百多吧。”
只听“噗——”的一声,金大力喝到嘴里的茶水一下被喷出两丈元!“啊哈哈哈哈!几十块、一百多……啊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几十块、一百多……啊哈哈哈哈……”他的大肚子起起伏伏,像一个快乐的大青蛙。如决堤洪水一样的笑声忽然戛然而止,他皱着眉,用手按着自己的肚子,嘴里哎呦哎呦低声叫了两声。“几十块、一百多……一个大男人,写啥狗屁诗呢,浪费生命!胜去我的工地打小工不胜?!”他终于忍住笑,双眼噙着泪花,万分鄙夷地说。
景爽低下头,羞愧难当,满脸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吱吱吱!”不知哪里忽然响起贪贪的叫声。
“是贪贪在叫!你把贪贪带来了吧,它在哪里……”金大力支起耳朵听着,问。
“在我的包包里,”景爽拿出金大力送给她的进口包包,打开盖子,贪贪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
金大力把贪贪捧在手里,从上到下抚摸着它的皮毛。“贪贪真乖,真有灵性。来,跳个舞,贪贪!”他把贪贪放到手掌里,说。贪贪便以金大力的手掌为舞台,跳起舞来,直立起来,挥舞上肢,单腿着地,原地旋转,还会弯腰鞠躬!
“哈哈哈!贪贪太可爱了,就像你一样。”金大力一面说一面用肩膀轻轻碰了一下景爽,满脸戏谑的笑容,瞅了景爽一眼。景爽嗔笑着瞪了她一眼,伸手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打了一下。
“这里暂时没事了,你可以下去了!”金大力冲站在一边的太监挥挥手,说。
“喳!皇上有事请按电铃,奴才随时恭候。”太监后退着出去了。
“娘娘!夜里咋睡,来朕的寝宫睡龙床吧?”金大力瞅着景爽问。
景爽低下头,面有难色。来了不是!这可怎么办……自己真是浑了头,明知道可能会有那个事,还跟他跑到这里,住这帝王套间,这一宿要花多少钱啊……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真要拒绝了,金大力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啥也没落着,岂不要恼羞成怒,翻了脸?!这个大款得罪得起吗……待要顺水推舟,又怎么对的起艾嘶鸣,她和艾嘶鸣的爱情来的多么不容易,前世要修炼多少年才能得到这正果,这样的爱情多么纯洁,多么美好,多么迷人啊,像海洋那样深沉、博大;如今,让她把这个海洋掀个底朝天,她不能够,也没那个力量啊……景爽的脑袋似乎有千斤重,她用手支着额头,大滴大滴的眼泪纷纷滚落下来,她用双手捂着脸,低声啜泣起来。
金大力一张大胖脸变成了黑锅底,僵硬地坐在那里,嗤地一声,张得很圆很大的鼻孔喷出一股粗重的黑烟——尽管此时他并没有抽烟,口气生硬地说:“你哭啥哭?!不愿意就拉倒,谁也没有把你咋着……”
贪贪觉察出气氛不对,转动着两只黑溜溜的小眼睛,若有所思,吱溜一下,从金大力的手上溜到景爽的身上,眨眼间没了,就像一滴水洇到了土壤里;贪贪钻到了景爽的心里。
景爽擦干眼泪,抬起头。唉!怪谁呢,谁让艾嘶鸣不能挣钱呢,爱情固然好,但是不当吃不当喝,自己不会和艾嘶鸣分手,但是也不愿过穷日子苦日子,打死也不愿意过……她倒在金大力怀里,说:“我喝多了……”
“这不就对了嘛!” 金大力脸上满天乌云风吹散,笑眯眯地说。他抚摸着景爽的后背,在她耳边说:“一会让宫女用步辇先把你抬到娘娘寝宫,再由娘娘寝宫抬到皇上寝宫。记住,千万别自己走着到皇上寝宫,免得宫女太监耻笑你!” 说罢,他伸手按响了茶几上的电铃。
…………
发展成情人关系后,金大力要送给景爽一辆宝马轿车,景爽思量再三,没敢要。艾嘶鸣出身贫寒,景爽的家境更差,她是贫困山区的孩子,如果她要了金大力的宝马汽车,艾嘶鸣问车从哪里来,她难以自圆其说。
艾嘶鸣和景爽结婚的日子就要到了,他一得空就忙于布置新房。这天,工人师傅把买的家具送到了,一样一样搬到楼上去,艾嘶鸣指挥他们如何放置。
一切都忙完了,送走师傅们,艾嘶鸣坐到崭新的沙发上,轻轻舒了一口气。空荡荡的新房里一摆上家具,就有家的味道了,有过日子的味道了。终于有一个所于自己的小窝了,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多么甜蜜的事啊!他憧憬着和景爽在新家里过日子的情景。
艾嘶鸣掏出手机,开始刷朋友圈、刷抖音消遣。一个小视频蹦入艾嘶鸣的眼帘:金大力和景爽在宾馆开房间,被金大力的老婆带着一帮娘家人堵住了,景爽衣衫不整,金大力的老婆和娘家人像一群狼一样撕打着她,金大力光着屁股奋力保护景爽……这个视频被刷爆屏了!
艾嘶鸣的脑袋里轰地一声爆炸了,他的眼睛瞎了,眼前一片漆黑,啥也看不到了;耳朵也聋了,啥也听不见了,这个世界一片死寂;快到夏天了,忽然间冷的像冰窖,他的身体像寒风中的枯叶不停地哆嗦……艾嘶鸣不知不觉中站起来,摸索着向窗户走去。他的腿“梆”的一声碰到茶几的棱角上,若在平时这么碰一下,他会搬起腿哦哦哦地叫半天,现在却一点不知道疼,一瘸一瘸只顾往前走。艾嘶鸣打开窗户,一股清风呼呼呼地刮进来……他盘腿坐在一片白云上,白云带着他往远处飞去,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成了一个黑点,最后完全消失了……
和金大力偷情的事曝光后,景爽一下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自己有何面目再见艾嘶鸣?!教师也当不成了……她像个木偶人,全身冰凉,眼神木呆呆的发直。金大力暂时也不能回家,就开着车带着景爽瞎转悠。景爽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啊,和她说话也不搭腔,脸白得像死人,眼珠子都不会动了……她如果神经了怎么办……金大力有些焦头烂额了。
天上阴云密布,隐隐地传来沉闷的雷声,开始下雨了。
车里突然响起邓丽君的爱情歌曲《水上人》,这是景爽的手机设置的铃声。美妙浪漫的歌声一遍一遍响起,景爽浑然无觉,毫无反应。金大力把车停到路边,向景爽说:“喂喂!你的手机响了……”他一面说一面帮景爽从包包里掏出手机,递到她手里。
“喂喂!!景爽!你咋不接电话啊……艾嘶鸣跳楼了,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你赶紧回来吧!”手机里爆出一串一个女性焦急的叫嚷声;打电话的是景爽的同事。
景爽丢掉手机,打开车门,从车里滚了出来。“嘶鸣!嘶鸣……”她叫喊着从地上爬起来,盲目地往前就跑,仿佛艾嘶鸣就在不远处,她几步就能跑到他身边。她往前跑了一会儿,感到不对,又折回来,往后跑,又跑了几步,还不对!在这半路上,景爽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地。她浑身瘫软了,紧紧抱着路边一棵大树,才没倒下。
“啊……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啊,我没出轨,嘶鸣你也没死,一切都是好好的,咱们五一就结婚!我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要了,当好教师就行,咱们永远厮守在一起……”景爽嚎啕大哭着说。“咔嚓”一声,一声炸雷在头顶响起,倾盆大雨哗地倒了下来。“我后悔啊……是我害死了你啊嘶鸣!你该留在这个世界上,该死的是我啊……我能用我的命换回你的命吗……我后悔啊……我后悔啊……我也不活了啊……”她一面撕心裂肺地哭喊,一面用头碰树,额头流血了,鲜血和着雨水泪水淌下来。
金大力从车上下来,冒着大雨去拉景爽回到车里,景爽死死抱着树不放手,仿佛和树连为一体了。他只好像落汤鸡一样又跑回车里,他瞧着雷雨里哭成一摊泥的景爽,恻隐之情油然而生,像罪人一样深深垂下头。
贪贪虽然存身景爽的心里,但也害怕这骇人的雷雨,便从景爽身上溜下来,跑到车底下,往外探着头,瑟瑟瑟抖作一团。
轰隆隆,哗哗哗,雷声雨声淹没了景爽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