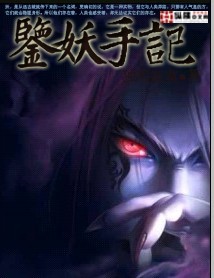天还未亮,空气中氤氲着一层湿润的气息,路上的灯很少,公交车在宽阔的马路上行使,将偶尔出现的亮光飞快的甩到车后。
车快到站时,透过朦胧的玻璃车窗,我看到前方街角处有一团白色的东西漂浮着,仿佛一团棉花糖似的,开始还以为是眼花,过了一阵才看的分明,它时动时停,颇有节奏一般,靠得更近的时候,它突然转过来,一张如浮肿的人的脸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两只眼睛鼓鼓的,眉脚下拉,很快就要哭出来似的,凭空看去,就像是某人的头挂在那里,这让正好奇打量着的我着实吓了一大跳,整颗心脏都快要跑出来。
这种东西绝对不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能见到的。我左右看了看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状,我又扭过头去看了看。
从它旁边经过的两个路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一般,依然谈笑风声,我知道我遇到奇怪的东西了,看那雏形,应该是幻在向怪成长,只是这样的嘴脸我真希望没有看到,太影响妖怪的形象了。
车刚到站,我就飞一般的下了来,这时候距离更近,让我看得更加清晰了些,原来这张脸是跟随在一个男人的身后不到五米,那男人走走停停,不时的往后望一眼,似乎感觉背后有眼睛盯着一样,狐疑的瞪瞪眼,发现没什么之后,又向前走去。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怪是靠人气成长的,而被吸收了人气,人很受影响,我猜测这怪是那一类型,既然被我遇到,我就没有理由坐视不理,至少要弄清楚原由才行。
大约跟随了几分钟,我看着那男子拐进了一个比较繁杂的街道,里面已经灯火通明,人也挺多,跟随在男子身后的哭脸左右徘徊了一下,渐渐的消失了身形。
"刚才那是什么玩意?"思索一阵不得要领,抽了支烟解乏。
"母厶。"一个声音响起,有些熟悉,我左看右看也没见有人。
"谁?"我警觉的低声问。
"某。"那个声音回答。
原来是霸下,我倒把它给忘记了。
"你认识那东西?"自己都是个小角色,哪有本事知道这些,我质疑的问道。
"某活了这么多年,见过的妖不说上万,至少也八九千,区区一个母厶,某还不至于认错。"霸下倒吹起牛来。
"你倒说说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能说清楚我就相信。"我笑了笑,看它能说出个什么事情来。
"某又没要让你相信。"霸下丝毫没把我的信任当回事,说完这句话,它真不再言语了。
"不说拉倒。"我也没指望它能说出什么来,当下一拍两散,脑海里却一直回想着那怪的模样,希望能从记忆中搜索到一点有关母厶的信息。
"要某说也容易,嘿嘿。"冷战不到两分钟,在我往家走的路上,它调我胃口道。
"貌似你说还有条件?"听它那奸诈的笑声,我想到了那天晚上它那有法调理的嘴脸。
"让你这右眼释放点妖力给某,某就告诉你。"果然是有阴谋的。
"等着吧!"它还以为那是我能控制得呢,"以为吃你家冰箱的牛奶啊!想要就要!"
真是指望不上,还是靠自己吧。
忙碌的时候很少抬头看,走在路上也只是自顾的向前,猛然停顿下来,看到一片枯涩的树叶犹如失去了所有的力气猛然得跌落在滚圆的石头小径上,挣扎着又随风翻滚一阵,才恍然发觉,我已忽略了太多的景色。
如此一本正经的忙碌,都是为了什么呀!
我叹了声气,自嘲的笑笑,但发现如此的笑声根本无法发泄内心的可笑情愫,随即蹲了下来,用手摁着额头,狂笑了几声,惊吓得附近的几个路人狂奔而去。
笑完之后,很多不知名的东西像汗水一样疯狂涌出体外,空虚与无力便随之席卷而来,缓缓站起身来,彷徨的四周望去,东南西北的景物模糊而快速的飞动,发现一切都与己无关,我就游离在世界之外。
开始想念父亲,母亲以及其他家人,他们那些原本熟悉的面孔渐渐不再清晰。
已经很久都没有回家,也很久没有听过家人的声音了,很多次我都是按下那些熟悉的数字,然后又消除掉。
我大概感情内敛,而父母又不善言谈,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彼此听到对方的呼吸,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短暂的交谈之后,余下的却是尴尬。
远远的有个小女孩手牵着一个氢气球走过,那一团白白的飘浮而来,让我眉头不由一皱,隐约间竟看到那张恐怖的哭脸。
母厶。
难道……
我有个念头一闪而过,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可有些不妙。
只能怪我太忙而忘记了这档子事。
来到上次遇到那个男子的那条街,时间已是晚上七点,这街附近房租便宜,所以外来人口很多,走近前去,就能闻到街道流窜出来的辛辣味与腥气,在这里各种小吃快餐店林立,忙碌之后的人们,喜欢在这里饮上几杯。
人很多,要找出一个人来无疑大海捞针,本想开口要霸下帮忙找找,毕竟妖对妖的气息比较敏感,但总感觉有些没面子,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好在街道并不长,来回搜索花不了多长时间,虽然知道那男子住这附近,却无奈不知道他何时会经过这里,到底还是比较盲目。
“他在左前方的第三摊位。”霸下的声音也算熟悉,这次它的口吻带着一丝居功和假装冷淡。
“你知道我要找谁?”按它的指示看过去,果然发现目标。我没告诉它要找什么,这家伙竟然主动告诉我,莫非它能猜测我的意图?
“某活了这么多年,见过的人不说上万……”霸下的这个话挺耳熟。
“不上次说的可是妖。”我反驳说。
“人和妖不都差不多,像你这样喜欢多管闲事的家伙,某见得多了,早就知道你放不下。”似乎有些轻哼,瞧不起我一般。
“真看不出你还懂人的心思。”我笑了笑,抽身向那男子走去。
那男子大约二十五六岁,而那张哭脸则停在不远处的街口,除了膨胀变大之外,并没有太多变化,我松了一口气,转头望向他,灯火光辉中,可以依稀看到他脸上的粗短胡须,头发临乱,卷着衣袖的衣服上还有各种白色的灰痕,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几碟小菜和两瓶啤酒,也没拿杯子,就着酒饼在喝,大概才喝了半饼,脸已通红,放下酒瓶之后,他又从兜里掏了几下拿了一包烟。
白沙,四块五的软盒。
再找火时,却怎么也找不到,然后他侧过头,准备叫老板。
我将手中的火机打燃递到他面前。
他抬头看了看我,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烟靠近些点上,他的手有些颤抖,深深呼吸一口之后,有些老毛病般的咳嗽了声,“谢谢。”
“不用客气,这附近都满了,你看我能和你并坐么?”我冲他笑了笑,摊手指了指其他地方。
他将自己的东西移过去些,“随意。”
算是接近顺利。
吸上一口烟,他会用大拇指蒽一下额头,闭上眼思考一会,然后重重的叹一口气。
看得出他心思很重。
我叫了半只烧鸭,一碟花生米,一盘凉拌海带丝,拿了两瓶啤酒,比起冷冽苦涩的啤酒来,爽口温和的米酒其实我更喜欢一些,但为了能和这位仁兄有些话题,我只好屈就了。
“一个人喝酒,多少有些闷,不如一起喝?”我提议道,然后又邀请他一起吃,桌上的菜我故意没有点重复。
“抽支?”他递上烟盒,抖了一支,算是回应了我的提议,“烟差了点。”
“哪有,这烟在这边很少卖。”一个地区的烟民有一个地区的口味,我拿了一支,自己点上,“老兄是湖南人?”
“湖北,在长江边上,望得见湖南,所以喜欢抽这口味。”他勉强笑一笑,动了动筷子,却只吃自己原先的菜。
“那我们算是半个老乡,我是湖南的。可惜没住长江边上,一直没机会见识。”我替他倒上酒,“为了这半个老乡,喝一杯。”
几口酒一下,两个人的话就说开了,他也少了当初的那许多拘谨。
“听你口音带点本地音,出来多年了吧?”我一直努力的把话题往心中的主题上靠。
“七八年了吧,高考那年惨败,就一个人跑出来了,一直都没再回去。”他忍不住猛灌一口,有些惆怅的叹了一口气。
“是有够久了。”我点点头,“怎么会一直都没回去呢?家里人应该很挂念吧?”说到后半句,发觉有些急切了,声音小了很多。
“我家就我妈和我,本来家里就很穷,我一读书就更穷了,原本想好好考上大学,让她高兴一下,没想到……哎,虽说出来了七八年,却一直混得没起色,根本就没脸面回去。”越说着他就越喝,我知道我的话触动了他内心。
听到他的话,我转头望向街口的哭脸,就如看到一个老妇人常年来思念自己的儿子而露出悲伤之情。
“这些,也不足以让你置自己的母亲于不顾吧?”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冷言这句的同时,我的心中也如被牵扯,疼痛不已。
他没有反驳,狠狠的用手捏灭了烟头,“你说得对,我一直就这样逃避着……这些天,我经常梦到她,常从梦中哭醒。”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有几个家人会责备自己的子女呢,你的平安大概才是她真正关注的东西吧。有时间的话,该回家看看了。”我站起身,眼角却在转身的一刹那湿润,这些话,我说给他听,其实,也是说给自己。
“是啊。是该了……”背后传来他的话,几个啤酒瓶倒地,旋转着发出乒乓的声响。
“母厶。就是母亲的思念啊。它不离不弃的跟随在儿子的身后,望穿秋水的等着儿子回头,那双眼,如果流下泪来,势必就是血泪,而母亲,大概也到了思念成灾,濒死不远了。”霸下颇有感慨的说。
“我早已经知晓了。她的形成,正是母亲的念,一个人的念在如此远的地方成了形体,身体大概早就脆弱不堪了吧。”坐在冰冷的河堤,烟火在微风中明灭,我的心依然平静不了,“只是这些人类的事,你是怎么知晓的?”
“无论人和妖,都是有母亲的啊,而且母厶这类东西,就算是妖怪自己或是能看到妖怪的人类,也看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霸下说。
听到此,我忍不住回头去望。
我的身后有母厶么?
我想问霸下,可最终没有问出口,我终于拨通了熟悉的号码,“妈,过几天,我回家来,对,公司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