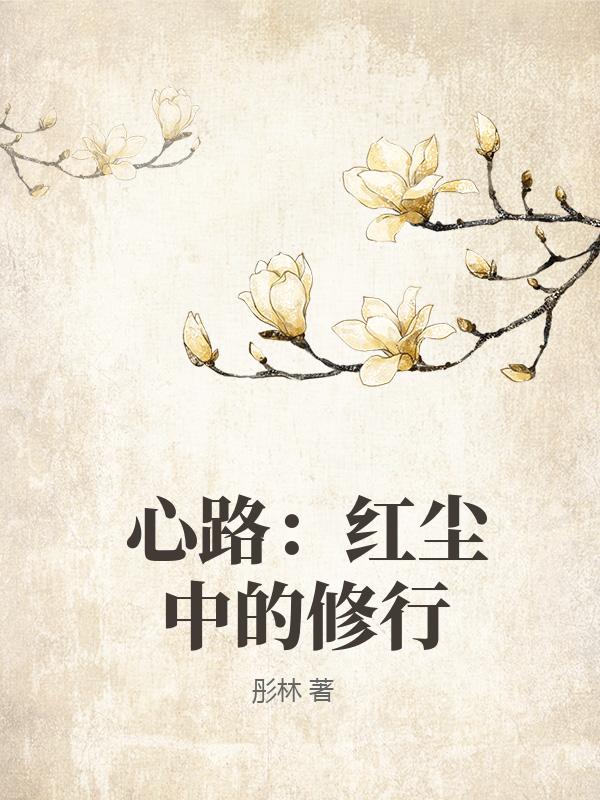第七章有为法
商学院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仅她一个,后来又来了几位不读学位的大陆短期交换学者。同时,还有一些来自美国本土、国府和港城的华裔留学生。大陆学生没来以前,国府学生一直是华裔学生中最出色的。自从辛潞入学以后,她就是绝对的第一,不仅在华裔学生中第一,在整个金融学系博士生中也毫无争议的第一。她极为宽阔、深厚的数学知识基础,在攻读多年后被定名为“金融工程学”的学科中,比所有的以传统金融学为基础的学生都钻研得透彻得多。加上辛潞在蚕场那些年不断挑战高难度学科的自学能力,不管遇到什么新课题,她比别人都快得多地跨越门槛,直击核心理论。同学们遇到难解的问题时,因为她能非常透彻地、触类旁通地准确叙述解读出来,在同学中她通常比老师还要受欢迎。
那个年代,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批以港澳台为主的华裔学生中,刚入学不久的辛潞就像个另类。尽管她的英文无可挑剔,气质也极为端庄,然而一个在偏远闭塞的农村中接受“再教育”了九年的知青,一身华朴巧拙、乡俗淳风,无论在生活习惯、对西方社会的见识、消费习惯、价值观还是日常谈吐上,还是和精致雍容、朱门绣户的华裔同学们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和隔阂。对东方文化不熟悉的西方人或许体会不到这种细微差别,但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中成长的华人中,这种差距还是极为明显的。不到一个学期的功夫,她在学术上就超越了所有的人哪怕有的是比她早两年就考进来的学长,遥遥领先了所有的人,却填补不了这种巨大的习俗差距。她生活得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学习、看书、进机房上电脑,辛潞很少参与社会活动。学生常去的餐馆、酒吧、舞会、影院、派对、演唱会,都极少见到她的身影。她若参加,一定是出于礼貌,被热心人硬拽去的。
许多人误以为她出身贫寒,来自偏远的乡村,除了擅长读书,文化艺术方面毫无造诣,音乐和舞蹈方面一无所长,因此对许多事物都不感兴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辛潞不仅钢琴弹得出色,还自幼能歌善舞。在出国培训班晚上开设的交谊舞班中,她以卓越的舞姿成为了众人瞩目的“跳舞皇后”,璀璨夺目。
有人问她:“你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好不容易来到纽约,怎么不懂得享受这么丰富多彩的生活?”
她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在克大商学院,除了学习,我还真找不到比学习更值得我喜欢的事。学习这么有趣、有价值的知识,难道还不够我享受的吗?”
面对这些花花绿绿的“有为法”,辛潞心中早就习惯按照金刚经说那样,视之为“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了。
在蚕场的九年里,辛潞习惯了从数学、英语和佛道经典中汲取知识、智慧与力量,也习惯了从释疑解惑、省悟明理的过程中感受内心的欢畅与怡悦。对她而言,这就是悟道谋道的乐趣——一种她修行以前无法理解的灵魂深处的意识觉醒和精神寄托。不真正踏入这条道路,是绝对无法体会其中的美妙的。修行过程,就是不断荡涤自己认知中的无明,从世俗习惯的感官喜乐中解脱出来。
不管别人怎么看,她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寂寞,经过蚕场的九年清苦的封闭生活,再寂寞再孤独对她来说都不会感到丝毫不适。纽约这个世界最发达最富裕也最开放的城市所涌现的各种新事物,使她接应不暇。克大图书馆里的书,多到她根本无法想象。何况她正在参与的研究项目,是世界金融学最前沿的探索,具有太多的挑战性和创新性,远比她自学数学理论复杂、困难得多。她潜在的所有能力都展现出来,她习惯了学习研究中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她满脑子都是钻研、探索、学习。她还经常去旁听一些关联的课程特别是从未接触过的计算机技术,经常“冒昧”地向任课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她的专业面很宽,理工科方面的知识也很全面,提出的疑问涉及的内容很深刻、面也很广,有时还难倒了老师。好在克大学风非常好,这种“冒昧”不仅促使老师主动和她私下深入交流探讨,还常常把她介绍给别的专业老师,因此大大开拓了她的眼界和社会关系。
同学中有位来自港城豪门的女同学温妮,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她对辛潞的英伦英语、英国文化素养、谈吐,特别是在金融学术上显露的锋芒,参与研究前沿项目的能力,一直到她的为人、品格都极为赞赏。把辛潞的情况通过越洋电话告诉家里后,港城的这家嗅觉敏锐的富豪家族对她产生了浓厚兴趣。温妮像个小跟班一样经常跟在辛潞后面。对辛潞来说,从蚕场到曼哈顿,这个巨大的环境转变中富家女温妮是个很不错的向导。她经常主动邀请辛潞一起逛街,不厌其烦向她介绍西方商业、市场、文化、上流社会各种习俗、生活方式,以及流行的奢侈品。对她融入当地生活方式颇有帮助。
港城人讲求现实,做事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温妮家的意思是笼络好辛潞,毕业后把她请到家族财务公司。这种罕见的,在美国顶级商学院中都名列前茅的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然而,他们眼界还是小了,辛潞的格局,不是用钱能衡量的。辛潞虽然对这些都毫无兴趣,但她感激温妮的真心情谊。只要对学习影响不大,她都会陪她,也常常在学习中照顾这位学妹。实际上,辛潞打工接触的美国上流社会圈子远远比温妮接触的层次要高的多,无论是那些豪华会所、消费场所、富豪们的聚会、参议员级别的交往,顶级的奢侈品定制商店,都远不是温妮看得到的。
或许正是因为她的孤独,在别人眼中充满了神秘感。加上翩翩若仙的气质、温柔娴雅的举止、靓丽的外表、高贵的谈吐、宽阔的知识面、显赫的专业水平,她成了大多数男生心中专注的对象。她经常收到别人的约会邀请、有意无意的搭讪。但凡此时,她那层曾经的坚硬外壳又撑了起来,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漠,浇灭了燃烧过来的热情。她修行以来,对爱恨情仇的主观认识已经炉火纯青。人世间那点卿卿我我的小伎俩,在心如明镜的她看来,和水中月、镜中影一般虚无缥缈。何况她心中早就有了高远,不可能再容下任何其他人。
她生活得很节俭,甚至节俭得有点“抠门”。一周上一次超市,买最便宜的面包,买最便宜的鸡蛋、包菜、土豆、胡萝卜,加点牛腱肉做一锅意大利乡下菜汤放进冰箱,再拌点色拉,能将就一个星期。整个黑龙江九年中,她就是天天只吃这几种菜这么过来的。她非常会做菜,但再好的厨师也欣赏不了自己的厨艺,她极少花时间下厨。
她身上穿的大多是离开魔都时妈妈从外贸内销店给她买的衣服。好在朱琴怡品味非常西化,式样也很前卫。在提倡“全棉”、“天然”的美国并不寒酸。其实她奖学金并不少,加上她假期还常去打工,而且打工的层次远比一般留学生高得多,不少五星级酒店、会所给的报酬比唐人街洗碗跑堂高上好几倍。因为在蚕场时长期生活在穷乡僻壤,根本没有机会消费,所以她很少花钱。“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各人的消费习惯,不会因为赚钱多少而一下子改变的。
辛潞一天大学也没有上过,她一直在担忧自己整个知识结构中因此存在什么缺陷,将来会影响自己的整体能力。所以,她花了大量时间去补充这些“错过”的大学专业知识。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担忧,或许不用两年她就能通过答辩而完成整个学位课程,拿到学位。即使她人为地拖长了课程,最后她还是比普通人快得多地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学习。当然,这些增加的付出也不都是白费。尤其是她在计算机科学上的深入钻研,使她具备了IT工科生的水平,为即将到来的计算机、互联网时代打好了基础。
很快,辛潞的博士生学位课程已经进入了即将毕业的论文答辩期。她从课程一开始,就进入了导师参与的一个金融预测工具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研究课题后来被命名为广义矩估计GMM,1981年公布,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个用数学方法去预测资本未来价格的方法,改变了过去依靠个人感觉、经验来预判的模式,成为日后大投资机构普遍运用的有效工具。因为参与了这个团队,辛潞也因此镀上了一层闪亮的金身,在日后的华尔街成为一段传奇。只有深刻了解行内的人才知道的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位中国姑娘,用出神入化的手段,一次次准确预告投资的走向,使一些机构在股市上大获成功。业内特别是那些大投资机构,对这位年轻的女金融分析师印象非常深刻。
教授带领这个团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芝加克大学主导的项目核心理论的研究,作为在整个研究中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实验、验证的一个合作小组,在研究过程中对实际应用和具体操作却是做得最多的,实际经验也是最丰富的。辛潞展现出了她深厚的数学功底,在以传统金融知识一统天下的商学院,她对金融的深入理解和对数学的透彻认知、数学工具驾轻就熟的运用,使她在这场模式破局中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这种金融数学两方面都极为精通的人在当时异常稀罕。教授也在她的协助下对整个方法顺利通过一次次测试、调校、验证、完善。终于在这个领域取得一席之地。她自己也因为一次次深入实践,不断提高了她对这套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和熟练技巧,在这个领域,她慢慢走到了实际应用的最前沿,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掌握并熟练运用GMM进行资产预估的专家之一。在GMM公布后,作为第一批研读涉及GMM的博士毕业生,业界专家们对她的有关论文十分关注,答辩时很多人都关心她究竟是掌握了真才实学还仅仅是赶时髦作秀,要知道,当时很多资深的专家都对这个工具一知半解,能照葫芦画瓢地运用的人都不多,大多数不知道其深层的理论依据,更是不能运用自如,洞彻事理。
答辩进行了整整一天,过程严肃、严谨、刨根问底。辛潞最后给出了一份令人敬佩的、无懈可击的答案。
一毕业,辛潞就收到好几家投资公司的聘书,开出的条件都非常优厚。教授向她推荐了一家投资机构,自此,辛潞正式步入美国华尔街金融界。从80年代起,美国的投资模式从主要以散户为主转为主要是机构投资。机构投资大量采用现代化数学模型预测,取代古老的依靠个人凭借经验做出的主观决定,正是这个改变,使GMM问世后立即投入实际应用,也使刚刚毕业的辛潞有了用武之地。
虽然她学习金融只有短短二年多,实践经验也非常有限,但她使用的这个方法表现出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力。进入华尔街后,她便很快发挥出她的价值。
就在她入行后几个月的一个傍晚,她接到周副领事的电话,告诉她朱琴怡已经离开了魔都,一天后到达纽约,还告诉了她航班号。她高兴极了,把家里收拾一下,准备接妈妈来一起住几天。自从她在华尔街有了工作,而且收入可观,她就换了套比较大的公寓。有三间房间,很宽敞明亮。房东还按她的要求配备了满屋家俱。现在,她算是站稳脚了。
辛潞到领事馆会合周副领事,一起乘车去肯尼迪国际机场,途中,周副领事告诉辛潞,她妈妈参加的是一个大型政府考察团,身份是副团长。其时,中国在纽约有两个常驻外交机构,一个是总领馆,还有一个是联大代表团。代表团比总领馆大得多,所处位置也更好,所以很多国内来的高规格政府团组都住在代表团,这次她妈妈带的考察团就将住在代表团。
“我还想接妈妈去我家住两天呢。”
“恐怕不行,她是副团长,不能离团。再说,在纽约只住三天,时间上也比较紧。”
尽管辛潞很失望,她还是非常识大局的。
接着,同来接机的一位主管经贸的领事问起辛潞工作情况,对辛潞这么快这么顺利融入华尔街感到非常惊讶,高度赞扬了辛潞的能力和努力,中国留学生中取得辛潞这样成绩的,极为罕见。还告诉辛潞,国内正在搞金融改革,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回去看看,出出主意。对此,辛潞一口答应,并告诉那位领事,只要国内有需要,随时可以通知她,她一定当成第一优先的任务去做。“这不是帮忙,而是使命。”辛潞认真地回答。
到达机场后不久,考察团就出现在到达口。辛潞忘情地冲了过去,紧紧抱住了朱琴怡。朱琴怡笑着对同团的同志们说:“这是我女儿,在这里读书,喔,不!已经工作了。”
看到周围纷纷投过来的惊异眼光,辛潞察觉到自己失态,赶忙退到一边。总领馆和代表团接机的人才上前一一握手,介绍着各自的成员。
大家一起到了代表团,辛潞就跟着妈妈进了她住的房间。妈妈高兴地抓住辛潞肩膀,注视着,笑着。“又长大了,现在像个职场精英了。”
虽然不能去辛潞家过夜,朱琴怡还是去辛潞住处坐了一会,辛潞又请她妈去了她刚来时打过工的法国餐馆。老板对她俩非常热情,还一定要赠送头盘和甜品,表达对辛潞这位令人难忘的中国姑娘的情谊。
朱琴怡悄悄跟辛潞说:“这家店看上去很贵吧?妈知道你的心意,但你这么花钱妈心疼。”
“还好啦,妈!天大地大,没有爹妈大。妈好不容易来一次美国,女儿不趁机报答一下几十年娘恩,怎么说得过去啊!再说,我现在有收入了,吃顿饭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什么了。”
“我刚来纽约时在这家店打过工,今天特地请你吃这家店的法国蜗牛和三文鱼。不像其他大多数餐馆,三文鱼是加拿大鳟鱼做的。这家店是从苏格兰进口的。”
“快告诉妈,这些年你怎么过的?怎么忙得一次都没有回国?”朱琴怡迫不及待地问。
首先,辛潞告诉妈妈,如果能早一些收到信,了解爸爸平反昭雪追悼会的具体时间,她无论如何都会回国参加。她渴望能够在众人面前,亲口对爸爸说出那铭刻在心底、反复诉说的心里话:“爸爸,您把您未走完的路托付给了我。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我选择的道路都将与您所走的方向完全一致——致力于国家的建设,让我们的同胞过上更好的生活。请您放心。”
朱琴怡告诉她,这些话她在蚕场写的信中多次提到过,追悼会上,她替女儿宣读了相似的这段话,使得很多参会的人黯然泪下,感动不已。
接着,辛潞又提到在这家餐馆、第五大道萨克斯百货打过工,后来又去了那个参议员家给那位富婆朗读莎士比亚著作,赚够了自己的生活费,也逐渐进入美国社会的经过。
“你在那个议员家做了多久朗读工?”
“不久!才三个多月。不知怎么的,议员那个哈佛毕业做律师的儿子得知了这件事,有一次开着跑车来学校接我,说顺路。我又不认识他,当然不会上他车。那次就没去。下一次那个开礼宾车的司机和他一起来,我才又上车去他们家。再下一次,那个公子哥儿竟然捧了一大堆花来学校,站在商学院门前向我求爱。扯不扯?!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
“就像你经常说的,随缘。”
“就是嘛,我去他们家又不是为了赚钱,我打工,主要是想要深入美国社会,多了解美国。是他们想多了!”
辛潞接着说,“事后,那个议员很不好意思。打过几次电话来学校,为他儿子的唐突向我道歉,并希望我继续去他们家朗读,保证他儿子不会再骚扰我,说他太太非常喜欢我”。顿了一下,辛潞接着说,“我还是没再去。不过,后来去希尔顿和几个高级会所打工,还是他介绍的。他认识的上层社会人很多,我借了不少他的光。”
“你今天这个英语水平国内无论哪所大学都教不出来的,”朱琴怡由衷地感叹道,“我真还没听说过有哪个留学生来了就能接触到美国的上流社会呢。”。
吃饭间,朱琴怡告诉辛潞,她外公从前是魔都有名的德昌洋行大班,魔都滩有名的买办,手下的代理商、经销商非常多。后来,这些经销商代理商都一一成了大气候,在世界各地都扎下了根。国家得知她这些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就让她带团去欧洲、美洲见这些她父亲培育起来的老板们,劝说他们来华投资。这些年,她跑了很多国家,其中绝大部分在欧洲,美国也来过两次,多数在西海岸,来纽约还是第一次。以前他们主动提出要资助辛潞的学习,朱琴怡没有接受。但以后可以保持一些联系,做他们这些华侨们的工作,这也是为了国家。
去年,她去了英国,见到了自己年轻时的闺蜜叶琳娜,叶琳娜告诉她,她父母隐退去了英国,住在东萨塞克斯郡的刘易斯,一个纯粹的乡间小镇。到六十年代末相继去世。叶琳娜特地开了几小时的车,带她找到了他们的墓地,去他们坟上献了束花。心里,她是愧疚的。父母生她养她,把她奉为心中的唯一,生命中的一切。本来她到红都后,她是可以有机会写信给他们,劝说她们接受自己的选择、理解自己的事业的。她相信对于自己当初救国救难、投身抗日的抉择,他们很可能会接受的。他们是买办,但从不做出卖国家民族的事。遗憾的是,她从来没有尝试过。
对于这两位自己从未见过的外公外婆,辛潞几乎没有任何印象,甚至连照片都没有见过。但她知道,妈妈的教养、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了解,乃至传给自己的优雅气质,都是来源于这两位老人。
说到自己的父母,朱琴怡感叹道:“现在,国内的风气是发财致富,人人都想发财当老板,很多人把自己的毕生所有都投入股市去赌一把,有点权力的就为自己谋私,想尽办法捞钱。你妈妈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一生下来就有数不尽的财富。可是妈妈还是背离了家庭,投身到一场民族救亡的血腥搏命中去,不要说钱财,连生命都朝不保夕。”
“妈妈,你后悔你选择了这么个人生吗?付出这么多,还受到这么多委屈。”
“不!妈妈从来没有后悔过。接触到革命理想后,妈妈就明白,人生有很多比钱财更宝贵,更充实、更高尚、更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妈有信仰,信仰是超越一切的。”
“妈,我理解你和爸爸,我尊崇革命理想,我也有过一样的理想追求,不顾一切地追随过革命。可是我像被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而且,我接触过的那些革命派、工人造反队、农场干部,给我的印象大多数是蝇营狗苟、损人利己,满口革命道理都是用来整治坑害别人的。慢慢的,我的理想淡漠了。我耻于和他们为伍。特别是爸爸的事,我对他们彻底绝望了。”
“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使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闪亮光辉或污泥浊水都毫无保留的摆到了明面,在这场动荡中,人们不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行为,而是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这种社会环境为沉渣泛起、蛇虫出没提供了条件。
马可思说,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变了,阶级地位也会变,因此思想就会变。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有什么政治立场,并不取决于他曾经的社会属性,而是他灵魂深处的思想意识。贫困,不一定孕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无私灵魂,不能自动带来高尚的思想品德。你见到那些损人利己的人,心底里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另一方面,你在农村九年,见到的农民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吗?”朱琴怡问道。
“不!妈,我非常幸运,在蚕场遇了到最好的人。指导员夫妇、何老师,还有赶马车的老张大爷。他们善良、富有同情心、对工作负责,对国家充满了感情。要不是他们,我不可能通过闻道悟道解脱思想包袱,早就沉沦在痛苦中,绝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辛潞感慨地说。
朱琴怡若有所思地说:“自从人类有阶级,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社会就有阶级之分,古今中国这样,美国也一样。马可思对于阶级和阶级社会属性的观点,永远不会过时。妈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却因为参加了革命慢慢有了个无产阶级的灵魂,你爸爸更是从未动摇过他的立场和信仰。你现在站到了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最高领地上,妈也希望你保持清醒,永远不要忘记你的根”
“放心!妈!我要是糊涂,早就钻营到纽约的上层圈子中去了。您别忘了,我可是具备布莱顿诺丁女校的潜质的喔。老子说:‘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若沉沦于财富,财富就变成困住灵魂自由的枷锁。我才不干呢!”
“不!未必!等你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后,真正的考验才到来。”
母女俩一直聊到餐馆人都走光了,才起身结账离开。
三天后,朱琴怡离开了纽约。
辛潞又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
命运似乎验证了朱琴怡所预见的情形,几年前辛潞做梦都无法想象的经济地位的颠覆性转折出现了。连续几年间,她在投资机构中所做的中长期决策,基于复杂计算得出的预测,最终都被证明极其准确。那些大胆依据她的分析进行长线投资的项目,均取得了丰厚的回报。辛潞因此在公司内部及整个业界声名鹊起,赢得了无数赞誉。除了年年攀升的高额工资收入,还取得了极为丰厚的奖励。
几家美国顶尖的金融机构纷纷向她伸出橄榄枝,公然挖她加盟。这一切使得她的前途看上去无比光明灿烂。随着进入美国收入最高的工作阶层,并在华尔街精英圈子里立足,辛潞的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华尔街历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能够达到她这个层次的女性寥寥无几,而作为亚裔尤其是中国人的女性更是绝无仅有。
除了面对没日没夜的工作压力之外,辛潞还频繁受邀参加各类上流社会的聚会。为了适应这些场合,她开始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鞋柜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衣橱挂满了高端定制的服装,洗手台上摆满了各种顶级护肤品。尽管如此,辛潞大多数时候依然异常低调,穿着简单朴素,很少化妆。她始终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金融界的细微观察与研究之中,关注那些常人容易忽略的细节与市场动向。
那个年代互联网尚未普及,辛潞一有空闲时间便钻图书馆,图书馆仍然是她去得最多的地方。
因为直接在金融界从事用GMM工具预测资产价值的走向,并成功证明了GMM的巨大应用价值,辛潞在业界内受到尊崇的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她频繁受到邀请去各个协会、学校、咨询机构做演讲、参加短期研究、在几个知名的咨询机构挂职。有的是教授拉她一起去,有的是她自己去。美国有点名望的商学院、研究机构她几乎都去过,美国金融界大多数名人专家她都见过、交谈过、探讨过。她已经成功踏进了美国金融界的学术顶层。而这些,后面都跟着很丰厚的额外收入的。辛潞银行账户里的钱财,已经不再有消费的意义,而变成了一长串数字。无论她怎么用,都只会增加得越来越快。
尽管辛潞已经跻身于上流社会,成为备受瞩目的名人,但她依然能从那些金发碧眼的同事眼中感受到一丝异样的目光。她能说一口令美国人崇敬和羡慕的不列颠英语,她的谈吐中充满了英国贵族阶级的典雅气息,这种气质让她在任何高贵的场合都能游刃有余。她举手投足间的从容与优雅完全融入了这些环境,并且她在华尔街的成功以及对新金融模式的学术地位使她成为了财富圈子里崛起的新星。
只要辛潞不主动提及自己的出身背景,几乎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她是来自英国的华裔富豪家庭。然而,一旦得知她来自红色中国,人们的反应首先是惊讶,随后便不自觉地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便如此,华夏——这片土地依然是她心底里最不容亵渎的骄傲,也是她不容选择的唯一归属。在那个年代,中国还处于相对贫穷落后的阶段,在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黑人。但是,辛潞从未因此感到自卑。
她坚信自己仅用三年就能够从一个偏远、落后的蚕场一步步走进华尔街,本身就证明了她具备不逊色于任何人的能力和智慧。
关于她的传言也传到了克伦比亚商学院,她的导师不止一次开导她安慰她:“你是我们商学院的骄傲,时间会替你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精英,你的将来属于美国,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差。”可是她心里却在想:“我为什么要属于美国?”一次次的心灵碰撞,她慢慢看清楚,她和美国的鸿沟不可能消除,她不愿,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华尔街资本这个圈子。
无论生活多么繁忙,辛潞总会在深夜时分,翻开何政赠予的那两本珍贵小册子,一字一句地细细品读,深深思索。虽然这两篇五千字的经典她早已烂熟于心,但每当思想或工作上遭遇难题,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翻到相关篇章,反复咀嚼,深入思考。其中,“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这句话,在这一刻尤其让她感触颇深。华尔街的奢靡繁华和谋道,不可能两者兼得。要继续谋道,就必须从富贵脱身。
随着辛潞的成功愈发耀眼,她在他人眼中似乎已成为上天眷顾的宠儿,财运亨通、富贵盈门,前程似锦。她所取得的地位令人羡慕甚至嫉妒,未来一定还有更多巨额财富唾手可得。然而,在这条铺满鲜花、通往光鲜亮丽的阳光道与继续充满艰辛的谋道路之间的十字路口前,辛潞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反思。她还记得出国培训时那位不认识的领导的殷切期望和“探路”金融学的托付吗?面对如此多的钱、名誉和地位,她还能守得住自己曾经的使命吗?
尽管道理显而易见,但置身于这天壤之别的抉择面前,正如朱琴怡所担心的那样,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道心不迷失自我?在清苦中坚守,远比拒绝华尔街的荣华富贵容易得多。她还能否坚守“空相”,不被财富蒙蔽双眼?还能否“功遂身退”,舍得放弃这泼天富贵,回过头去“安贫守道”?
蚕场六年的修行,佛祖的“不住于相”、老子的“独泊”,曾使她在清苦孤寂的极度搓揉挤压中保持道心,今天,换成了荣华富贵的巨大诱惑,同样是对心灵的极度撕扯挤压,她同样需要保持道心。如果这道坎过不去,只能证明她修为太低、道行太浅。苦和富两个极端,在《金刚经》看来,同样都是虚幻,都是对身心的有为法,都是心灵自由的桎梏枷锁,都要看空。看空富贵的过程,就是在富贵中的修行。
与此同时,心底深处还有一个声音始终提醒着她:“爸爸希望我走的路,一定不是一条追逐金钱的道路。”这个刻入骨髓的声音像是一盏明灯,指引她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世界中确定自己的定位,继续前行,继续探寻爸爸托付给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