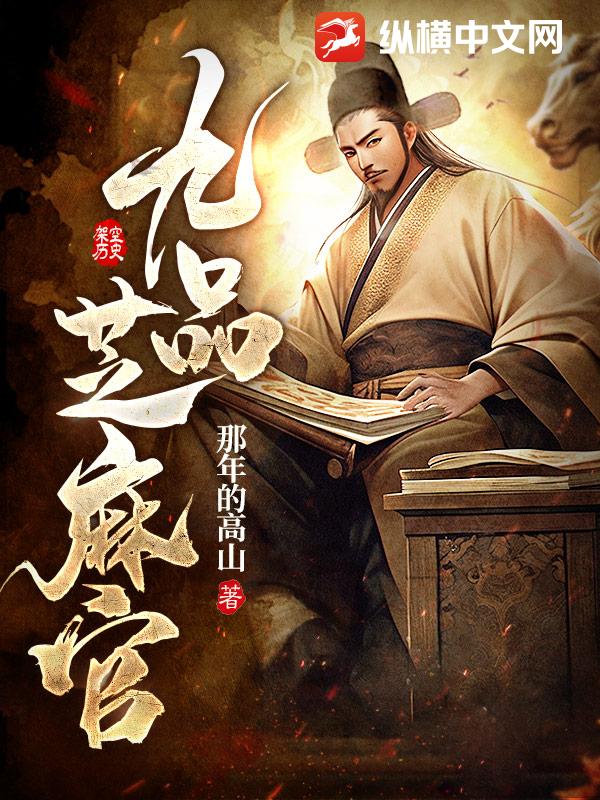南方富庶,也没有存粮可售?
陈处墨听岳父这么一说,心头一阵发慌。即便是剿除了海寇,商路畅通,然而无粮可购,幽州就得面临饥荒之患了。
“南方河道纵横,灌溉不成问题,又没有旱灾、雪灾,怎的也没有余粮?”陈处墨不解的问道。
“一来,是南方有水患威胁,粮食减产。二来,是富豪大户囤积居奇,把收获的粮草囤在家中,只待价格上涨之时再出售。”方总镖头看似粗鲁,说话倒也有条有理,众人听了连连点头。
“岳父大人,依您之见,该当如何?”陈处墨问道。
“贤婿既然认识林相,让他打开金陵的粮仓,就当是赈济北方了。”方总镖头提出了建议。
“处墨早就跟林相、白少卿谈过了,朝廷存粮也很有限。西南旱灾,中原蝗灾,用来赈济的地方还很多。”陈处墨叹息道。
大夏王朝虽然商人比较活跃,总体说来,还是处于“农业社会”,老百姓靠天吃饭。若是没有饭吃,饥荒爆发,流民就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处墨,我们手里有蒸汽船,可去东瀛、暹罗、爪哇等地购买粮食,直接运去幽州。”方芷寒眼睛一亮,提出一个建议。
“这些地方资源贫乏,自己都不够吃,哪有余粮给我们?”陈处墨摇头否决。他在扬州结识了不少商旅,从他们口中探听了不少海外消息。
若是东瀛富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花,那就不会出现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木村等失势武士也就不必出走海外,充当海寇了。
东南亚一带的暹罗和爪哇国,接近热带,气候炎热,农业很不发达,更是没有指望。
“南方富户自有余粮,可以向他们高价购买。”方芷寒又说道。
“女儿,为父已经试过了,收获很小。南方佬精细得很,不到高价,不会出售粮食。”方总镖头叹息道。
“岳父大人,不能光盯着大州大府,南方各郡县的财主和商贾,多半家有余粮。当前扬州一带,一石米多少贯?”陈处墨问道。
“二百文。”方总镖头答道。
按照大夏的标准,一贯钱相当于一两银子,也就是一千文。照此来算,一两银子可购买五石粮食。
“南方粮产比北方多,粮食价格也不便宜啊。”陈处墨叹息一声。
昔日扬州一些富商和海寇手下甲贺忍者勾结,出卖大夏军政情报。被陈处墨抄家后,除上缴国库,还私吞了四十万两。再加上卖煤挣钱、南方富商献礼,以及朝廷拨款,手里足有七十万两银子。
然而,蒸汽机和火炮的研制,就是一个无底洞,已经有将近六十万两银子投入进去了。手里资金有限,只有十万两可以购粮。
“依岳父所言,当前扬州粮价是二百文一石。换算过来,就是一两银子购买五石米。处墨有十万两银子,可以购买五十万石米。”陈处墨掰着手指计算。
“贤婿所言不差。”方总镖头点头说道。
五十万石米,听上去挺多,实际上也只够十多万人食用一年。陈处墨陷入沉思:如何才能用手头仅有的十万两钱财,购买更多的粮食?
李元芳习武之人,对于买卖毫无兴趣。他建议道:“陈大人有剿灭海寇之大功,南方商户都尊称您为陈海王,多半会给您面子。不妨由您亲自出面,让南方佬自愿放血,拿出粮来。”
“商人以逐利为先,他们虽然现在捧着陈某,可若是陈某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不会惯着我。说服他们自愿交粮,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应当出钱购买。”陈处墨摇头。
思来想去,陈处墨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
“岳父大人,芷寒,元芳,你们行走江湖多年,见多识广,可否知道商品的供求规律?”陈处墨笑着问道。
三人大眼瞪小眼,不知陈处墨说的是什么意思。
“贤婿请讲,老夫洗耳恭听。”方总镖头说道。
“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规律,指的是指商品的供求关系与价格变动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必然性......”
陈处墨在穿越前学过经济学,一阵名词如连珠炮一样迸了出来,听得三个人目瞪口呆,如在云里雾里。
方总镖头看了看女儿,一脸疑惑。方芷寒满脸懵懂,微微摇头,表示自己也听不懂。
陈处墨又继续解释道:“供求变动可以引起价格变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就要下降......”
“说人话!”方芷寒不耐烦地打断了丈夫的讲课。
“娘子勿要心急,听处墨细说:市场上的米如果多,价格就会下跌;如果米少,价格就会上涨。为今之计,就是咱们想办法,让市场上的米多起来,才能压低价格,低价购买。”陈处墨解释道。
“这个......粮价不是官府定的嘛?为什么市场上的米多了,价格就得下跌?”方总镖头一头雾水,听不明白。
“咳咳,处墨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假设一个村子,只有一个年轻待婚的小伙子叫狗剩,同村一个年轻姑娘叫翠花。狗剩想要娶翠花,就要出彩礼一百两银子。他要是不肯出彩礼,翠花的父母就不让女儿订婚,把狗剩打出去。”
陈处墨一脸笑意,举了个例子。
“这彩礼不便宜啊......”李元芳叹息。
“假设这村里有十个年轻姑娘,狗剩就会硬气起来,对翠花的父母说:彩礼减半。若是不答应,老子去找其他姑娘了,不稀罕你家闺女。”陈处墨又说道。
“我明白了!物依稀为贵,若是泛滥成灾,就会贱卖了。”方芷寒一拍大腿,恍然大悟。
“哈哈,娘子真是冰雪聪明!”
陈处墨心花怒放,一把揽住妻子。方芷寒顺势一肘,疼得陈处墨龇牙咧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