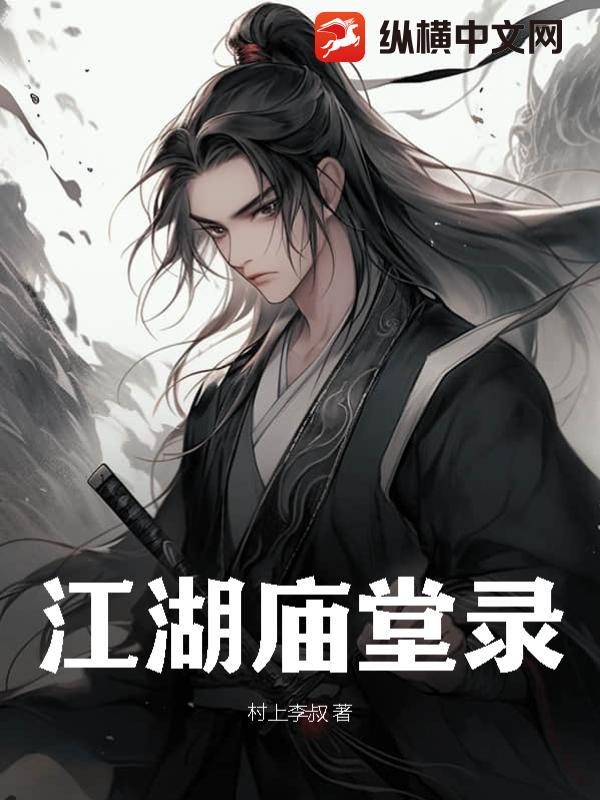旧国重臣遗孤还能在北卫武将中占据或不可缺的地位,不是李善顾惜以往所犯下的重罪,施恩于下一辈人中,的确因举贤不避仇在北卫军中得到重视,这才有能者居多,不计出处的功勋。
施种道,与十三太保中排行高过自己一头的人物有过节,不过旧怨归旧怨,在他们这一代,就变成了相互较劲,暗自比拼,势必在军功上压对方一头,或许是他的身份特殊,得不到重用,无论做什么努力都总是牵强了那么一点,不如回自己辖地内舒舒服服地治理军务。
还有一人不得不提,就是白甲白盔的十三太保之首,此人复姓诸葛,单名一个彪字,世人称呼“小兽王”,北卫真正的兵人,杀人如麻,用兵如神,几乎凭借一位旧国将门之后身份,屡次被朝廷加封,军中地位在年轻一代中无人能出其右。
传闻虎生三子,必有一彪,此人完全符合这一特性。
他是北卫众多武将之中,唯一一位正统将门之后,不过这个正统是他的祖辈,换到如今这个王朝不过就是旧国余孽,在那个各路诸侯混战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寻常百姓为了活命,奔走迁徙之外,如不是迫不得已,绝不会遗弃亲生子嗣。
诸葛彪却是例外的存在,毕竟在他上面的几位兄长,皆在旧国中担任军阵要职,使得他就相形见绌,被其父视为不成气候的废物,还在三四岁的时候,尚且记事,其父因卷入一场宫帷政变,重罪下狱,永世难得翻身,他上面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一家老小深受牵连,几乎要断绝他这一脉,不得不东躲西藏,整日食不果腹,只得丢下他,这样才能保存家族命脉与火种,就是这一无奈举动,在他幼小心灵间萌生出报复的仇恨。
他独自在深山中靠着吃树叶、草根勉强活着,随着年纪的增长,也学会了茹毛饮血的本事,直到十一二岁,活脱的一只野性难驯的野兽,无意中发现了猛虎与野猪间的赌上性命的死斗,野猪体型巨大,以经验判断足有六七百斤,整日在粗壮的树干上磨蹭,打磨皮毛,甚至会到有泥泞的腐沼里寻觅食物,练就一身皮糙肉厚,寻常的刀刃利箭根本难伤其分毫。
反观猛虎,虽体型与野猪相近,利爪、獠牙、粗如人臂的尾巴,无不触及即伤,碰上即死,一旦被其盯上,山中的任何野兽终难逃丧其于血盆大口之下的下场。就连像人一样站立的棕熊都能与之斗得有来有回,双方落得两败俱伤,谁也奈何不了谁。
唯独对面的野猪成精,不惧猛虎的爪牙之利,就是凭借刀斧难伤的皮毛,还有一对尺许长的獠牙,横冲直撞起来宛如一辆勇往无前的战车,将猛虎撞得晕头转向,对于行动迅捷异常的野猪根本无计可施,最终伤了那头兽王一条前肢,悻悻败逃而去。
若不是野猪累了,口吐白沫,说不定靠着绵长的耐力,能将老虎变作那日的饱餐。
自那以后,他暗自立誓,要像野猪一样,成为整个山林中的王者。
他后来加入到了李善的队伍里,凭借着一身肝胆,勇往无前,建立了不少惊世之功,而他由一名奋勇杀敌的无名小卒,成为李善麾下最年轻、最能打的校尉,足足用了八年,直到他麾下有了自己的旗号,“彪”字营成了第二天,他找到了曾经遗弃他的爹娘、兄长、姐姐们,一一将其报复致死。
两个姐姐都嫁了人,连同她们的夫家,三位哥哥和其子嗣、嫂子,上至七十老叟老妪,下至咿呀学语的孩提,共计二十八口,无一幸免。
待彪长大之日,必是原虎族覆灭之时。
诸葛彪换了姓氏,拜山中野猪为师为父,从此李善军中也多了一位百战百胜的得力先锋武将。
他素来目中无人,在场其他太保也唯有他率性自然,就连熊能行军作战稳健,胡不归其行如风都自愧不如,非常之人定有非常之处,在整个北卫三十二万铁骑中已然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并非他特立独行,而是整个北卫其他各字营几乎把他孤立起来,毕竟能做到他这个地步,难免树敌众多,北卫前二十年是李善一人独撑,后十年就非他莫属。
既然义父已经做完指示,诸葛彪也就不用呆在这里跟大伙儿怄气,他们不待见自己,自己也看轻他们,个个的争风吃醋,能将嫉妒自己人这份心思在北卫防务与战局谋划上,比什么都强,他行军布阵从不请示,李善特赦既是均旨,难不成今日留下来吃顿饭再走?
他从小就饿怕了,当年加入军伍时,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能管饱饭吗?
李善看着这个毛头毛脑的小子,全身上下伤痕累累,新伤复旧伤,一身山里野兽皮毛简单缝制,就成了他的衣衫,眼里透着瘆人的杀气,对待任何人皆是一副敌视,惊起了心中的好奇,对他投以温和的笑意,诚我不欺地答应道:“有饭吃,只要你凭本事,多少都管够。”
也自那之后,诸葛彪再也不用在各种野兽嘴下讨食,换成了需要与人拼命的战场上杀人,待得胜归来之时,就往火房跑,连李善的庆功宴席都等不及,他饭量极大,一顿饭要吃足足三五寻常兵卒的量,因为他真的不想再忍饥挨饿。
太保中有不少情同手足,也有相互对立仇视,都是明面上争功,暗地里较劲,从未像他一样茕茕独立,自然引来众怒,不过妒忌也好,树敌也罢,都是为一人效力,也说不上谁好谁坏,反正忠于一人总没错,有什么异议,大可以较量一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目了然。
许多说不通,想不透的腹诽,李善作为北卫统帅,做了决定即便是大错特错,在北卫等同圣旨,轮不到将士上下评头论足,这才是任人唯贤、能者居上的用人之道,至于举贤不避仇,任人不认亲这种道理,谁有本事也绝不会被埋没,谁没有本事,就算是亲生子嗣也绝不例外。
北卫只认军功,不讲情面,每个人都是实打实一场场苦战、大战熬出来的,更是用一兵一卒的性命换来的。
看着白盔白甲的诸葛彪体型臃肿,大摇大摆地走了,毫无一点留恋,甚至跟李善告辞客气的招呼都没有,堂而皇之地带着副将、亲信,回他的属地军帐。
他毋须客套寒暄什么,在场的任何人既不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更非他一心对付的敌人,没有挽留,也只是一心放在军政要务之上。不是他与大家关系紧张,而是他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他走,那个施种道自然也跟着走了。
诸葛彪掌管着北卫最能打仗的龙珠军,下属百兽营都统就是施种道,诸葛彪这个征西将军都走了,施种道作为其麾下的副将,难不成要顶头上司把自己的军务也一并打理安排了不成?
李善看着二将离去的身影,说不出的得意与欢喜,仿佛庆幸北卫军伍中有他们这般尽心尽责之人,北卫雄甲天下也无可厚非。
何况作为北卫大元帅,自始至终也不喜欢虚头巴脑地客套,或许有一个“六狗子”苟新就够了,多了就会败坏军伍中风气,更会令大未朝廷那边嫉恨,已经恨之入骨了,难道还要被那些政见不合之流授人以柄,说北卫专养闲人,还会被朝廷抓住辫子不放,拥兵自重却不念社稷稳固,一心只想封侯拜相等诸多口舌,李善都是一笑置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李善本在风口浪尖,被天下人罗织各种罪责,恨不得将他打入万劫不复,要是空拥有三十二万铁甲,不做保家卫国之事,他自己一刻也坐不住。
李善清楚,与这些得力肱骨武将们,谈论军机要事依旧是一副我行我素的姿态,从不加以绳检克制,自己本就是一个洒脱大度之人,有其父必有其子,底下有一两个义子像他也不奇怪,喝了酒也不知说得是醉话还是戏谑,淡淡地道:“各自既然要忙就去忙吧?说不定清闲日子没几天了,边境防务也好,征北大计也罢,我也能轻松一些,再说什么事都要孤身去躬亲垂范,就是没日没夜都忙不过来,眼下紧跟着朝廷要孤去大内述职,北卫总不能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吧?”
他说得很直接,也很直白露骨,但话糙理不糙,要不太保们个个都是自己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除了争风吃醋就是你咬我一口,我背后使绊子,什么上下一心,就成了笑话了,一个个不作为,不上进,不为北卫尽心尽力,却做那种阴险小人,专门对付自己人岂不是打自己脸。北卫根基尚且不稳,外有虎视眈眈的柔然大军,内有大未朝廷不断施压,天下人无数双眼睛紧盯着他,犹如风雨中惨败摇曳的破舟子,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胡不归与其他竭诚报效的武将们也恨不得早些离开,能不见义父最好,毕竟刚一战下来没有半点军功不说,差点损折两支精锐在北境,义父表面上什么都没有追究,是给二人留有面子,给足了台阶下的,实际上是让各自知耻而后勇,这次的惨败暂且记着,非要板子真正打在身上才知道痛,难道胡不归是那种记吃不记打的蠢驴,还用明示?
刘豫不敢迁怒于谁,也暂时压下火来,自己本事不行,勿怪苟新等人嘲笑。
其他太保也不轻松,义父留足了面子,也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坏了气氛而已,诸葛彪、施种道表面上看似不合群,其实最是知趣,非要李善下了逐客令再走?又不是三岁小娃娃,什么事都要言传身教?早些回各自营地里着手处理军务,这才是最明智选择,既为义父分忧,又为朝廷解困。
半个时辰后,大帐内,烛影煌煌,形单影只。
李善在中军帐内踱步,思绪万千,似乎为什么事发愁,竭力压制却还是难以释怀。
老管家负手而立一动不动,大将军没有任何示下,也没有说一个字,半个时辰了整个大帐内鸦雀无声,是不是几位军功卓著的义子们开始沽名钓誉了,没有当初起事时的雄心壮志,有的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有的开始不再那么忧国忧民,军政大事如同当天和尚撞天钟——得过且过;甚至有的压榨百姓,享受荣华富贵;而有的开始疯狂敛财,中饱私囊;更有甚者觉得时局卜定,不惜找后路……北卫还是以往那个北卫?
老管家不敢说,也不能说,一个字也不提,原因很简单,这些人都是跟随大将军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皆为袍泽,没有他们,北卫就没有今日,说不定还是那个烽火连年,外虏欺凌,内忧不断,饿殍满地,粥妻鬻子的混乱年代。
这些人之所以受朝廷册封,对北卫,对眼下的大未都功不可没,何况个个都是李善心腹爪牙,他们各自能有今日辉煌一大半出于李善栽培,更何况稳固朝廷与北卫之间关系,与那些皇室宗亲,达官贵人分庭抗礼,十三太保实力不容小觑。
李善一心栽培他们,能得此殊荣,是自己一手造就,当初想稳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同时作为一大底牌,但凡朝廷要削职罢免他这个大将军,十三太保就会领兵造反,三十二万兵马足可以横扫整个大江南北,有他们在,朝廷就不敢轻易动他丝毫,然而他选择裂地封侯,屈居于北卫苦寒之地,做起了固土守疆的忠诚武将,就这样还招来政令不合之人的诽谤与眼红,所以才落得一身骂名。
李善但凡有半点心思造反,也等不到现在,何况三分天下的局面,无论是大未还是南梁,都会投鼠忌器,现在与大未君主平分淮河以北又有什么不好,虽不是帝王,却近似帝王,做皇帝很辛苦的,孤家寡人,落得一个冷冷清清,无人可信,那才叫一个可怜,还是北卫现在这样挺好,和和气气,都是一家人。哪像帝王家,父子反目,兄弟手足相残,为了坐上那张龙椅,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不可谓不残忍,心肠不可谓毒辣狠烈,已经丧失了一个人的感情,真是验证了自古无情帝王家这句警示格言。
他没有造反的心,底下的却不怎么想,堂堂太子少保,即使官至五品,在整个朝廷也是有头有脸的功勋,唯独李善限制了他们,他在北卫一日,就不允许任何一个义子出任朝廷官职,十三太保,保的不是大未任何一位未来储君,而是整个北卫和天下的黎民百姓。
太保也不是大未的太保,空挂一个虚名,在北卫不能有出将入相的野心,只有一心为北卫百姓守护安宁的必死决心。
生在北卫,战死北卫。
可惜他老了,有的人不这么想。
人心复杂,心各有异。
谁还能保持当初那颗至纯至善的心?
朝廷这些年明里暗里使花招,李善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不过谁又能保证每个人还是那样心地淳善?说不定早已按捺不住,私底下与朝廷要员,政务上德高望重的大臣们接上了头,甚至密谋私商,毕竟皇帝跟他这个大将军都老了,他们还年轻,新君登基,难免自谋出路;或许新君上位,北卫早已变质,就连大未都变质了,何况旧人自该退位让贤。
李善凭一己之力在北卫与大未之间斡旋,身边除了长公主这位的大人物,还有就是朝廷这些年来安排进来的贵胄儒士,谁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嘴上不说,不代表这些暗度陈仓的事就没有,这是要提前为未来军国大事着手准备了啊?
“你说我该不该把兵权交出来?”李善这句话似乎在问原来的总教习,现在却像一家人一样那么亲切,不分彼此、甘愿瞻前马后服侍将军一家老小的老管家。
老者素来慎言,不敢对时局动荡,军国大事吱声半句,他还是垂手负立,似乎这个中军帐有他不多,无他也不少。
李善就当是在自言自语,不过他也知道,问道于盲不等于老管家也有异心,他跟在身边时间最久,快三十年了,毫不夸张地说,他自小与李善撒尿和稀泥一块长起来的,后来跟着他出来一起打天下,最是胆小,也没什么主见,大字不识一箩筐,要不是当初受李善怂恿,说不定早些年战火纷飞时就横尸乡野了,一身戎马,孤苦无依,念及旧情,李善才放心把他留在身边,他是一个勤勤恳恳、忠厚实在的人,到如今却无处可去的孤魂野鬼而已,倒不是李善可怜,而是三十年的生死至交,值得这样。
柴老米,这就是他的名字,一生为李家鞍前马后,训练出的士卒更是不计其数,长得一副慈眉善目,一到了沙场上杀敌最是心狠手辣,北卫从上到下,只要是正规从北卫调教出来的,就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在他一番调教之后,也无不挂念这位老卒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