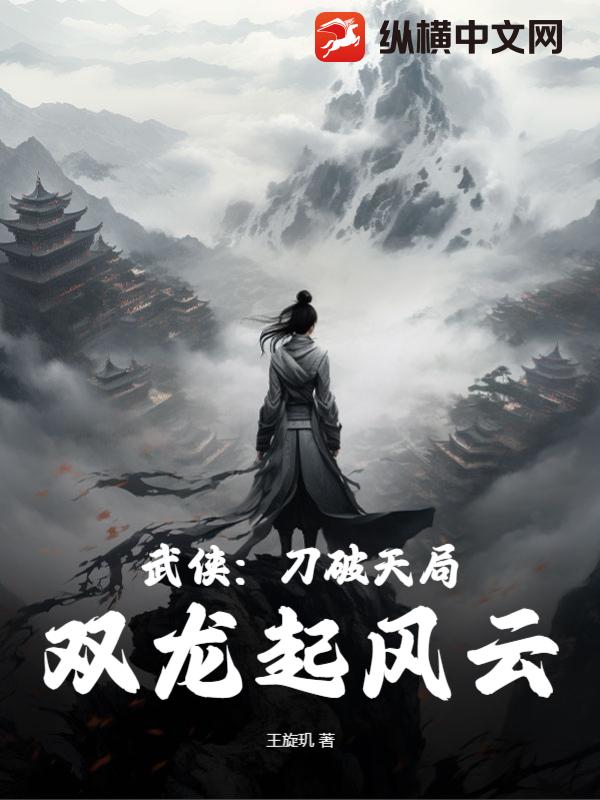“你打算如何收留他呢?”司华容又问。
“弟子受戒五年,稍有所成,不知可否收徒?”艮门这条分支上有了司华容、柳岚烟师徒,要收个弟子当徒孙,令子孙庙一脉相传,也是合理。
“这也得请示住持。”
“师父能否作主?”
司华容觉得好奇,为何柳岚烟一直想避开住持。
说真的,他本人也不太喜欢住持,该人是个笑面虎,极难从脸上看出心事,按理说学道之人务求清静寡欲,此人却热中于政治,常常结交教内教外道俗人物,颇有要做一番事业的气势,或许说管理偌大一个道观就需要此种人物,但他的野心恐怕不仅于此。
“家有家规,”司华容说,“这男孩也不是借宿一两晚,住持这一关在所难免。”
“如此……”柳岚烟踌躇着道,“可否容我思考三两日,待这雪天过了再做决定?”
“你要师父瞒着众人?”
柳岚烟揖手道:“还请师父成全。”
司华容低头不语,拿起经书别过头去,良久才说:“什么样的大雪天?冷杀人,这种天气会上山的人准是疯了。”说着,轻轻扬了扬手,示意柳岚烟和阿瑞离开。
柳岚烟会意,拱手作揖道:“谢谢师父。”便拉了阿瑞出去。
多年后,阿瑞已忘了他到长生宫的那一晚,毕竟很少人能保有三岁的详细记忆,而且当时他已经冷得无法言语,心里想的只有食物,还一直惦念着那位说要去拿食物的守门道人,依稀还记得外公跟他说,迟些会来接他走。
自有意识以来,他就只接触过外公和阿母,阿母无法照顾他,而外公会带着他在山林中觅食。
当他还幼小走路不稳时,外公会用布条将他系在背上,待他可以在崎岖的山间走路后,外公便教他走得更快、更敏捷的方法。
他不知道,外公符十二公是江湖中奇门之术的高手,然奇门之术在有明一代属于禁学,私学者有被杀头的可能,又由于奇门乃兵学秘术,在天下动荡之际,有心谋天下者,更会将符十二公视为奇葩以据为己有。
然而,符十二公并不擅长于武功。
他懂得在山林中求生,但无法保护外孙日后不被人杀害。
所以他必须找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教导阿瑞如何保护自己。
这一切阿瑞并不知晓。
不仅如此,只不过两年后,他还完全遗忘了这位自他出生以来就照顾他、呵护他的外公,更加不会记得外公说要回来接他的承诺。
若是要阿瑞回忆最早的记忆,他会说是小时候跟业师柳岚烟学“青城十八式”时,每天早上摸黑起床,在院子里一步一式的练习。
小孩子贪睡,晨起是苦差事,何况是寅时(凌晨三点至五点)就爬起床?因为师父要在卯时参加早课,只好这么早就练拳。
师父告诉他:“凡是要练『武功』的人,都应该吃饱睡足,但要练『道功』的人则相反,必须吃得少、省着睡。而且不论是武功或道功,练成之后,尤其必须压抑自己,不轻易使用。”
年幼的他不明白:“不使用的话,练来干嘛?”
师父摸摸他的头:“刀剑乃杀人利器,要是你手上有一把剑,你要不要去杀个人试试?”
阿瑞摇摇头:“无怨无仇,哪可轻易杀人?”
“正是,这种道理五岁小孩也懂!”柳岚烟道,“武功乃修性之术,古人云:『学武一道,非有坚忍不拔之志者,难得有大成功;非忠义纯笃者,难得有大造就;非谦和恭敬者,难得有好善终。』你看学武之人若是横行霸道、自恃高强的,有几个是好下场的?”
“可是,”柳岚烟又说,“五岁小孩不懂的是,即使有怨有仇,也不许杀人。”
“为什么?”阿瑞不解的歪头,“我听师父说的故事里面,人家不是都要报仇的吗?”这也难怪,中国自古崇尚报仇,尤其为父母报仇,特别受人赞许。
“因为没有人希望死。”
阿瑞低头想了一下。
“即使是虫蚁也不愿死。”柳岚烟又说,“咱们学道之人求的正是不死,与天地同寿,是不是?”
“是。”
五岁的阿瑞当然不会想到,这一段对话将影响他一生,尤其是二十年后当他面临抉择的那一刻,决定了他将英年早逝抑或年老善终。
阿瑞也不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朱九渊的那一天。
朱九渊是长生宫的住持,还在壮年就力排众议,接管了住持之职,据说是他的“离门”业师极力推荐之故,而他也果然不负所望,将长生宫整治得有声有色。
司华容跑去见他,说为徒弟找到了一位徒弟,继承艮门家业。
“什么来历?身家清白吗?”朱九渊依例问道。
“实不相瞒,是个我家的远房表亲,幼失父母,年纪才三岁。”
“既是司老修行的亲人,当然没问题,”朱九渊知道司华容德高望重,自然会卖人情,“不过人才三岁,还不便受戒,需等到立冠方可。”
于是,阿瑞没有马上见到朱九渊,再者住持公务繁忙,也就没有执意非见到阿瑞不可。
如此一晃眼就到了次年的五月初一“延生节”,传说当天是太上老君传“三天正法”给张天师的日子,青城山又曾是张天师降魔驱鬼的地点,山上各宫观也免不了庆祝一番。
这时,住持朱九渊特别召集了长生宫所有道人,讲了一番《道德真经指归》的道理,那是西汉时代解释《老子》的书,将老子“自然无为”与儒家“仁义道德”统一的作品,目的在讲述经世治国的帝王之术。
朱九渊最后结论说:“可见老君所说自然,也并未置民生疾苦于不理,这层道理,张天师最懂,所以才能代代相传,至今五十二代焉!”
“住持所言何义?贫道不懂。”有位年轻道人如此问道。此人乃“坎门”弟子,专习内功,以拂尘为武器,道号“明镜使”,取自禅宗六祖慧能《坛经》典故:“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
朱九渊点头道:“可记得第三代天师张鲁?其时西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张鲁以我教率领民众,杀官攻城,雄据汉中,令四川一带民生安乐,达三十年。诸位同道,道法自然,张鲁所为,焉不自然?”
众道人之中,有人缓缓点头,也有人垂目养神,朱九渊精目一扫,便已心里有数,随即又船过水无痕似的慈目微笑道:“是以今日延生节,感谢老君传法于天师,令天下庶民,得永生大法。”
众道人谢过了住持讲经,正起身退出,朱九渊瞄了一眼柳岚烟身边的阿瑞,指着问道:“柳爷,那位可是你徒弟?”
柳岚烟作揖道:“尚未正式入门,端看他日长大,有无出家意愿,再行定夺。”
“甚好。”朱九渊低首转身,又忽有所感问道,“徒弟什么名字?”
“小名阿瑞。”
阿瑞直看着朱九渊,没开口说一个字,因为师父要他不说话,怕说了话会惹祸,这些年来,他也习惯没需要就不多说、有需要也不需说了。
“阿瑞,”朱九渊面对他道,“你将来想出家吗?”
阿瑞依旧眼愕愕的望着他。
朱九渊也不强迫他回答,顺口再问:“几岁?”
“四岁。”阿瑞很快回答。
朱九渊的脸色有那么一瞬间僵了一下,眼神中竟掠过丝毫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