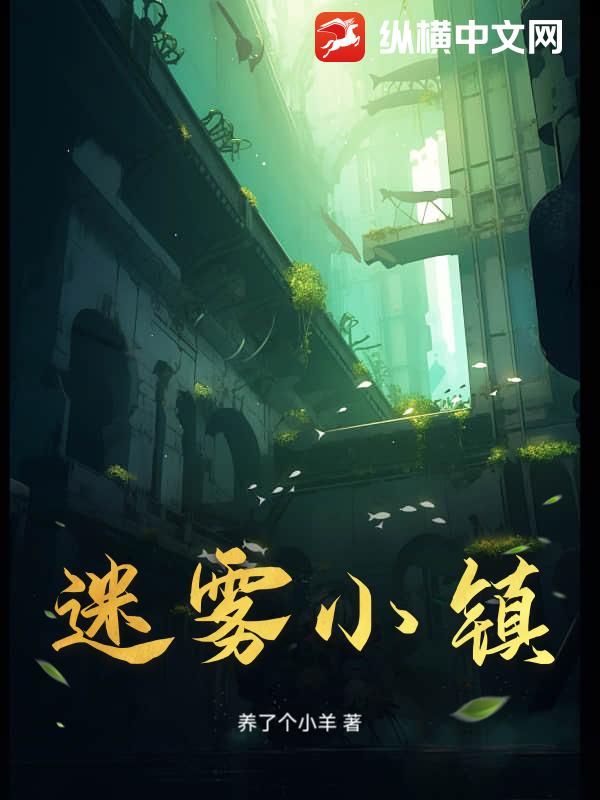
第一章 异常信号
夏令营的老槐树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灰绿色的叶子蔫蔫地搭在枝桠上。
树底下那排红砖平房更显破败——墙皮褪成了病态的浅粉,露出底下斑驳的黄土。
屋檐下挂着的三角旗原是红黄蓝三色,如今被晒得发白,风一吹就软塌塌地耷拉下来,像条没力气的舌头。
报名处的木门吱呀作响,黑板上“自然探索夏令营”七个字被雨水泡得发糊,粉笔末子顺着木纹往下淌,像一道道浅灰的泪。
旁边歪歪扭扭添了行小字:“为期两周,包食宿”,笔锋潦草,透着股“能凑活就凑活”的敷衍。
木门上贴着张活动表,“采集标本”的“集”字被虫蛀空了下半截,“篝火晚会”的“火”字只剩个黑糊糊的轮廓,倒像是真被火烧过。
林小满的粉色行李箱“哐当”一声磕在门前的石子路上,她没管箱子,反倒踮脚抓住根低垂的槐树枝,盯着叶背上一只青黑色的毛毛虫看。
“小满!跟你说的话听见没?”妈妈的声音从身后追过来,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急,“在这儿老实待着,别天天追虫子抓蚂蚱,让人笑话!”
林小满回过头,高马尾随着动作甩了甩,发梢沾着片槐树叶。
她穿件明黄色的短袖,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小臂上几道浅褐色的划痕——那是上周抓螳螂时被草叶划的。
“知道啦,”她含糊地应着,眼睛却瞟向营地角落的篱笆,“妈,你看那丛草,是不是有动静?”
爸爸蹲下来帮她提箱子,眉头皱成个疙瘩:“跟你王叔说好了,这营地便宜是便宜,但你得守规矩。去年你把邻居家的鱼缸拆了找蝌蚪,今年可别再……”
“知道知道!”林小满没听完就往后退,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个放大镜,“我去看看环境,你们赶紧回去吧,车要误点了!”
话音未落,人已经像只窜天猴似的扎进了营地深处,明黄色的身影在灰扑扑的平房间一闪,就没了踪影。
妈妈望着她的背影叹气:“这孩子,哪像个十二岁的姑娘家……”
爸爸摇摇头,拎起空了一半的背包——里面原是塞满了连衣裙和童话书,全被林小满偷偷换成了捕虫网、镊子和一本翻烂的《昆虫记》。
林小满没往宿舍走。
她的放大镜扫过仓库墙角的蛛网,网眼里卡着片灰黑色的羽毛,边缘泛着圈焦黑,像是被火燎过。
“奇怪。”她嘀咕着捏起羽毛,指尖能摸到焦痕处粗糙的质感,不像普通野鸟的羽毛那么顺滑。
顺着篱笆根往前走,草丛越来越密,隐约能闻到股腥甜的气味,混着泥土的潮气,有点像下雨天死老鼠的味道。
她拨开一丛狗尾草,心脏突然“咚”地跳了一下——三只芦花鸡歪在草丛里,脖子以不自然的角度拧着,原本雪白的羽毛沾着泥污。
最显眼的是脖颈处那圈焦黑的爪痕:五根趾印分得很开,边缘卷着焦糊的毛茬,像是被烧红的爪子狠狠攥过。
“不是野狗。”林小满蹲下来,放大镜凑近爪痕,“野狗的爪印是圆的,这是尖的,看起来还带倒钩……”
她伸手碰了碰鸡身,已经凉透了,但羽毛底下的皮肤却有点黏,沾了点黑灰色的粉末——和刚才那片羽毛上的焦痕粉末一模一样。
“喂!你在那儿干啥?”一个粗哑的声音突然炸响。
林小满猛地回头,看见管理员老王拎着串钥匙站在仓库门口。
他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沾着油污,看见草丛里的死鸡,脸“唰”地白了。
“王叔,”林小满举起放大镜,镜片反射的阳光晃得老王眯起眼,“这鸡是被啥东西咬死的?你看这爪痕,还有焦黑的印子……”
老王慌忙冲过来,抬脚就想把死鸡往草丛深处踢,却被林小满伸手拦住。
“别碰!”她的声音突然拔高,带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这痕迹不对劲,可能是……”
“哪有啥不对劲!”老王的声音发虚,眼睛瞟着别处,手忙脚乱地把死鸡往麻袋里塞。
“就是山里的野獾,饿疯了跑下来的,我这就处理掉,不耽误你们夏令营……”
他的手抖得厉害,麻袋口没扎紧,一只鸡的腿掉了出来,露出脚踝处更深的焦痕,像被烧红的铁丝勒过。
“野獾又不会用打火机。”林小满盯着他的眼睛,“王叔,你是不是知道啥?”
老王猛地直起身,额头上渗出汗珠,他把麻袋往身后藏了藏,干笑道:
“小孩子家别瞎猜,赶紧去领营服,一会儿要开营了。”
他推着林小满往宿舍走,脚步匆匆,麻袋里的死鸡硌得他胳膊直颤,“这事我来处理,保证不影响你们玩,啊?”
林小满被推了两步,突然挣开他的手:“我去告诉其他同学,这里的野獾很危险,让大家小心点。”
“别别别!”老王赶紧拉住她,脸都快贴到她脸上了,“这要是传出去,家长就不让孩子来了!你王叔就靠这营地支个零花钱,算叔求你了,这事……就当没看见,行不?”
他从口袋里摸出块水果糖,塞到林小满手里,糖纸是皱巴巴的橘色,“听话,啊?”
林小满捏着那块硬邦邦的糖,看着老王扛着麻袋钻进仓库后墙的阴影里,麻袋底拖过地面,留下道黑褐色的印子。
她低头看了看手心残留的焦黑粉末,又抬头望了望营地后方那片墨绿的山林——风从林子里钻出来,带着股潮湿的腥气,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着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