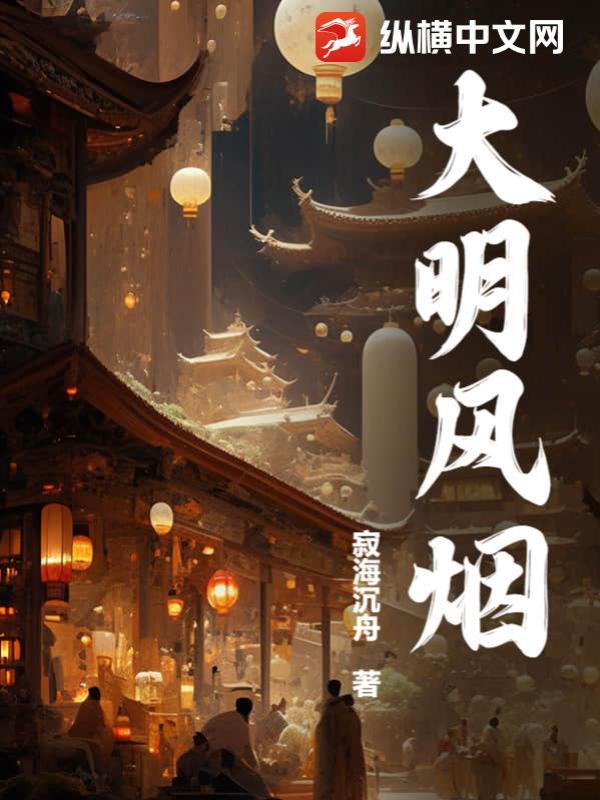
楔子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
大明新都顺天府皇宫,武英殿。
戌时末,夜已经深了,大明当今皇上朱高炽一身素服坐在案桌前,一张满月脸上不显威严,却是尽显仁慈,宽大臃肿的身材直接就占去了案桌长边的一大半。
之所以大明皇帝身着素服,是因为自永乐帝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塞外回程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不过刚过去四个月,现下尚在国丧期。
苦坐东宫二十余载,朱高炽登基继位也仅仅三个多月,尚未新年,属于他的年号“洪熙”也尚未启用。
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刘保在旁伺候,从一旁小太监手中接过一道茶盘,上面是一盏茶水,他伸手试了试盏外温度,然后小心翼翼放朱高炽身前的案桌上,“主子,茶沏好了。”
他曾在东宫伺候近朱高炽近二十年,鞍前马后,对朱高炽的起居习惯最是熟悉。
太子继位,东宫旧人升级为皇宫内臣,这几乎是历代铁律,原因自然是一来信任,二来用的顺手。
朱高炽自为太子时,勤政之名便享誉朝堂内外,夜里几乎从不早睡,不是批阅朱棣派人送来的奏章,就是与东宫的辅佐大臣们议政,颇具朱元璋和朱棣的风格,而每到这个时候,必然要饮上一杯产自浙江的顾渚紫笋提神,一种始于唐代的皇家贡茶。
战战兢兢当了二十多年储君,登基之后,他依旧如此,不曾改变。
朱高炽端起茶盏,饮了一口,满意地点点头,这才对在下首正襟危坐的内阁首辅杨士奇道,“杨师傅,一个月前,察合台汗国遣使吊唁先皇之时,持察合台和鞑靼两国国书,极力促成我大明、察合台汗国、鞑靼三方联盟,一同征伐瓦剌,只是当时先帝梓棺尚未入陵,朕未置可否,现在鞑靼新立的大汗阿岱又呈递国书请求和谈,商议来年出兵瓦剌之事,如此步步紧促,你如何看?”
杨士奇曾为太子少师,朱高炽尚在东宫时便对其多有倚重,尊重有加,直至登基,便让他代替杨荣做了内阁首辅,凡事都要过问他的意见,甚至私下里仍称他为“杨师傅”,杨士奇多辞不允。
杨士奇知晓皇上深夜召见自己是为此事,闻言起身道,“皇上,察合台汗国使臣前脚刚走,旬月鞑靼便遣使呈递国书请求和谈,臣以为这只能说明鞑靼现下处境堪忧,可能是真的被瓦剌逼急了。”
朱高炽笑道,“西有瓦剌,南有我大明,鞑靼的地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处,那阿岱汗和阿鲁台焉能不急?”
“皇上说的不错,月前察合台汗国遣使,想要促成三国联盟,此事看似察合台汗国主议,实乃鞑靼在背后极力促成。先皇在位时,曾五征塞外,使前元余孽对我大明再也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功莫大焉。”
杨士奇说到这里,话音一转,“不过五次征伐,四次是与鞑靼作战,对漠西的瓦剌却是鞭长莫及,只能坐视其逐渐强大。如皇上所言,对现在的鞑靼来说,西有瓦剌,南有我大明,生存空间狭小,他们必然是不愿看到被瓦剌吞并,进而统一整个蒙古草原,多番权衡之下,这才有了两次呈递国书之事。”
杨士奇现在这个“内阁首辅”头衔可非朱元璋和朱棣时期的谢缙、黄淮等人可比。其实纵观整个大明朝,内阁首辅从未成为过正式的官职,在杨士奇之前,最初就只相当于皇帝身边的谋士,只有区区五品,位高但可不是权重,手中并无实权。
但从杨士奇开始,朱高炽就给他加上了兵部尚书、吏部侍郎的头衔,“内阁首辅”由此才真正做到了“位高权重”,直至后来嘉靖万历时期的张居正,达到内阁首辅的权利顶峰。
可以说杨士奇就是大明朝内阁首辅登上权利巅峰的开始。
朱高炽闻言,深以为然,手抚下颏不住点头,“杨师傅所言极是,那我大明眼下该当如何应对才是最佳?”
杨士奇道,“皇上,对鞑靼来说,西面的瓦剌是他们的灭国之危,对我大明来说,亦不能忍受一个强大的瓦剌将来虎踞北方啊。”
这句话就表露了他同意和谈的意思。
这话正合朱高炽心意,“杨师傅,有父皇的功绩在前,现在想要彻底消灭鞑靼,举手投足之间,但对我大明而言,却不见得是最好的策略,整个蒙古草原,从西到东,察合台汗国、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卫,哪个是善茬?消灭其中一个,只会强大另外三个,这仗是打不完的。”
眼见朱高炽与自己意见相同,杨士奇立刻道,“皇上英明,臣认为现下我大明要做的,就是不能让蒙古草原再出现一个成吉思汗一样的人物!瓦剌的首领脱欢曾被阿鲁台击败,俘为家奴,如今逃脱之后居然还能率领瓦剌对鞑靼成碾压之势,此人堪比古时卧薪尝胆的勾践,不可不防啊。”
这话说到了朱高炽的心坎里,他不断点头表示认同,可随即又皱眉,“朕何尝不知现下三国联盟对我大明有利,只是父皇因北征鞑靼驾崩不过数月,之前察合台汗国的提议,朕虽未置可否,却已经招致不少文武官员上书劝阻,现在便与鞑靼和谈,是不是有些仓促了?”
杨士奇道,“皇上考虑的是,先帝驾崩未久,便与鞑靼和谈,的确是让朝堂众臣难以接受,尤其是那些追随先皇和鞑靼打了二十多年仗的武臣。”
他说到这里,抬眼观察了下朱高炽的神色,“不过皇上,国家大事可不能意气用事,当分析利害,朝臣的意见需当想方压制,臣觉得鞑靼太师阿鲁台应当也是知道和谈阻力重重,所以才会选择先帝驾崩之后,拥立鞑靼新汗阿岱,然后以他的名义经察合台汗国促成联盟之事,如此大费周章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为开辟新象,减少阻力。”
“你说的不错。”杨士奇的一番话让朱高炽一扫犹豫踌躇,“阿鲁台的确是被瓦剌逼急了。”
说完又想了想,脸上浮现不忍之色,“只是即便同意和谈,与鞑靼共击瓦剌,父皇在大漠多年征战,虽战果卓著,但百姓也多有疲敝,府库空虚,若现在还要用兵......”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朱棣当年多用兵,导致府库空虚,百姓疲敝,现在上位的他不想再劳民。
杨士奇道,“皇上仁慈,爱民如子,大明朝虽国富民强,但也经不起连年用兵,如今鞑靼已然对我大明构不成威胁,但坐看鞑靼被瓦剌吞并进而做大,甚至一统整个蒙古草原,也不符合我大明的利益,既然现在鞑靼要和谈,还要商议来年联盟进击瓦剌之事,臣认为皇上完全可以利用鞑靼的处境,尽可能争取条件。”
他看着朱高炽,“皇上,臣认为大明可不出兵。”
“不出兵?”朱高炽听闻欣喜,双手撑在案桌上想要站起来,但他身材肥胖,腿上又有疾,一时踉踉跄跄没有成功。
“主子当心龙体。”一旁伺候的刘保赶忙上前搀扶。
“皇上当心。”杨士奇一大把年纪,也是赶忙上前。
朱高炽笑着摆摆手,“杨师傅,不碍事,有什么好办法,你快些说来。”
“是。”杨士奇道,“皇上,阿岱汗和阿鲁台现在面临的是鞑靼的生死存亡危机,对于他们来讲,首要的,是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所以大明可以答应两国修好但不出兵,同时承诺约束关西七卫,让他们与察合台汗国放心东西夹击瓦剌!”
朱高炽皱眉道,“如此条件怕是阿岱汗和阿鲁台不会答应吧?”
“皇上,臣还未说完。”杨士奇笑道,“臣来时听闻钦天监近来测观天象,说近来多见云遮月,今年将是罕见寒冬,塞外生存尚属不易,想必鞑靼来年进击瓦剌也不会顺利,为长远之计,大明的条件最多可提供些许粮草,以助击败瓦剌,削弱脱欢实力,如此阿鲁台必然答应!”
“好!”朱高炽眼睛一亮,“不劳民,不出兵,好一招坐山观虎斗,如此甚好,就依杨师傅之见!”
说罢看了一眼案桌上阿岱汗呈递的国书,眼中闪过一丝担忧,“杨师傅,这鞑靼新立的阿岱汗尚且不知根底,但鞑靼太师阿鲁台与先帝交战多年,此人阴险狡诈,善谋利害,曾多次诈降,不可不防,纵然现在鞑靼在河,大明在岸,也不能小觑呀。”
“皇上所虑甚是。”杨士奇也看了一眼案桌上的国书,“阿岱汗在这国书里是邀皇上共商,但现下正值国丧,先帝驾崩又与鞑靼相干,无论如何,皇上也不可行,依臣之见,当派一得力干臣作为钦差,前往鞑靼主持和谈及之后联盟共击瓦剌之事,阿鲁台即便有诡道,也当及时处置。”
“如此甚好,那以你之见,谁人可担此大任?”朱高炽问道。
杨士奇眉眼一低,稍稍琢磨,立刻抬头,“臣举荐一人,可不负皇命!”
“谁人?”朱高炽立刻问道。
“广西按察使胡概!”
“胡概?”朱高炽听了一阵迷惑,他从未听过此人。
杨士奇道,“皇上,胡概乃是臣的同乡,不过他虽在广西任职,但现下却不在广西,永乐二十一年,因在广西多有政绩,臣已举荐他暂任浙西巡按御史,专司剿匪之事,这一年多来成果颇丰,浙西多年匪患已平息许多,对推行王化再也构不成威胁。”
朱高炽闻言大喜,“此人真能担此大任?”
杨士奇保举,“皇上,臣观胡概,将来必入可为相,出可为将!”
 书友63928297
书友63928297厚着脸皮自己给自己评价
2024-05-02 19:15:48 ·属地未知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