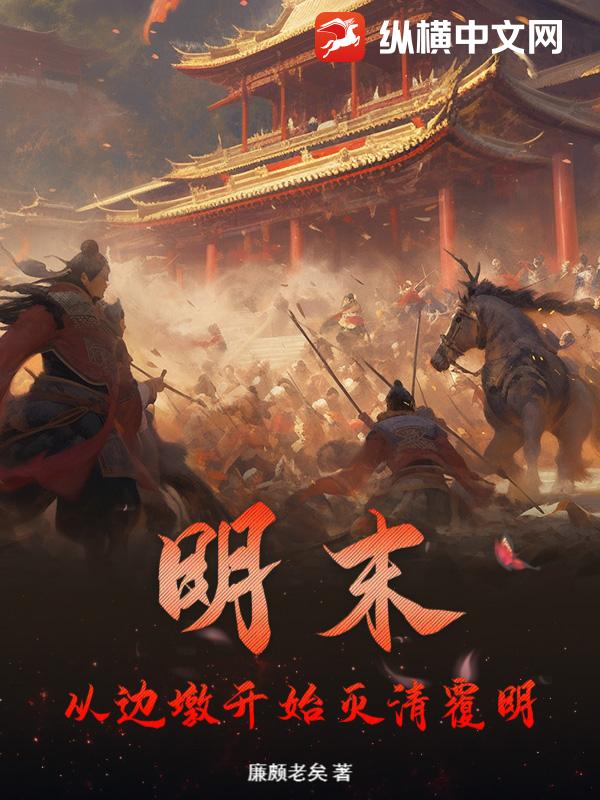
崇祯七年,天灾肆虐,山河破碎。
三月,陕晋大旱千里,赤地焦土,饿殍遍野,民易子而食,惨不堪言。
四月,李自成汇合张献忠,铁蹄踏破河南,陷澄城,烽火照中原。
七月,塞外铁骑骤至。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分三路破关而入。宣大防线顷刻崩摧,烽燧连日狼烟,虏骑所过之处,村墟尽毁、城郭为墟,血染边关。
在这尸山血海之际,现代顶尖雇佣兵唐骁,魂穿明末,沦为宣府镇最底层的小小墩卒。
外有建奴铁骑踏破山河,内有流寇蜂起祸乱天下,朝廷腐败至根,军中粮绝刀锈。
但他眸中冷焰,从未熄灭。
手中锈刀,亦可杀人......
目录(共 27章)正序
进入作品目录 查看更多第1章:这墩,我要了!
黄风呼啸,卷起千堆沙。
一道身影却在沙暴中稳如磐石,手中一杆长枪刺、扎、撩、崩,招式简练狠绝,枪风撕裂空气,带起的杀意竟比刮骨的寒风更刺人。
忽然,动作戛然而止。
唐骁拄枪而立,任由黄沙扑打脸庞。
三天前,他还是叱咤风云,灯塔黑榜第一的顶尖雇佣兵。
而今,却魂穿到大明崇祯年间宣府镇,一个被欺压、最终累死的边墩小卒身上。
此时,皇太极正率领鞑子大军肆掠宣府,大明内忧外患。
身为军人的他,很清楚,乱世之中,刀兵才是硬道理。
三天的忍辱负重,不仅是为了熟悉这具身体与原主的记忆,更是为了摸清这墩里每个人的底细与提升自己的武力。
如今,身体已大致掌控,武力也有保障,人心也已看透。
现在......
唐骁深深地吐了一口浊气:“是时候行动了。”
他的目标清晰无比:先拿下这座边墩,以此为基,在这崩坏的世道中,杀出一条血路!
沉默片刻,他挑起水桶,朝着那座熟悉的土围子走去。
......
第四火路墩,气氛很是压抑。
肥头大耳的墩长吴用正叉着腰,唾沫横飞地训话,一双小眼睛扫视着面前面黄肌瘦的军户。
“鞑子祸害了良田,上头震怒了!张大人下了死命令,地必须补种上!”
“完不成任务,咱们全墩上下,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得吃军棍!”
“到时候别说种地,屎都拉不出来!”
他吼得声色俱厉,目光却下意识瞥向角落里的夜不收韩从和刘仲。
那两人一个抱臂冷笑,一个嘴角讥讽,让他心里发怵。
他不敢使唤那两个狠人,小眼睛一扫,落在狗腿子秦通身上。
“秦通!明天起,盯紧赵良、马秋,还有那个闷葫芦唐骁!”
“天不亮就赶他们下地,谁敢偷懒,扒了他的皮!”
“是!吴头放心!”
秦通腰弯的像虾米,谄媚至极,转头看向赵良几人时,却瞬间换上了一副趾高气扬的恶相。
“吴…吴头我……”
赵良脸色惨白,怯懦地挪上前:“我那几亩活命田也叫鞑子祸害了,求您宽限两天,让俺先种上自家地,不然…不然明年我...我得饿死啊。”
忽然,一个尖酸刻薄的女声就像淬了毒的针一样,从吴用身后的房门里猛地刺出来!
“哟——”
“赵良,几日没敲打,你皮痒痒了?”
话音未落,吴用的浑家王氏就探出了那张瘦长的马脸,一双三角眼恶狠狠地剐着赵良,嘴角带着鄙夷的冷笑。
“行啊,老娘现在就让你去北庄,找张管队给你松松筋骨!”
自从他们的儿子攀上了北庄管队张士贵,成了上门女婿后,这王氏和吴用就真把这第四火路墩当成了自家的王国,作威作福,把墩军全都当成了可以随意驱使的奴仆。
“张管队”三个字如同一声炸雷,吓得赵良浑身一哆嗦,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脸色由白转青,死咬着嘴唇不敢再吭一声。
北庄的张士贵,那就是这里的土皇帝,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得罪了他的人,就没一个能全须全尾的。
旁边的马秋更是吓得魂不附体,死死缩在赵良身后,脑袋都快埋进胸口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看到这一幕,韩从与刘仲交换了一个眼神,皆是微微摇头。
世道如此,欺软怕硬已是常态。
这事与他们无关,两个见惯了生死的老兵也懒得管这闲事,只是心下对这群人更看低了几分。
秦通一见自己露脸巴结的机会来了,顿时像打了鸡血,一个箭步窜到赵良和马秋面前,指着鼻子痛骂:
“你家那点破地算个屁!能跟张大人的军令比?”
“吴头把这任务交给咱们,那是看得起咱们,是给咱们在张管队面前露脸的天大机会!你们倒好,推三阻四!”
“真是一点都不知好歹,活该穷死饿死!”
这话说得极其诛心,仿佛不去给吴用种地就是天大的罪过。
赵良和马秋气得浑身发抖,胸膛剧烈起伏,干最累的活的是他们,挨最毒的骂的也是他们!
可看着秦通那副狐假虎威的嘴脸,再想想他背后的吴用,两人最终只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死死攥紧拳头,把滔天的委屈和愤怒硬生生咽回肚子里,忍气吞声。
吴用正眯着眼,十分享受秦通这番阿谀奉承。
就在这时,唐骁挑着两桶水,步伐沉稳地走进了院子。
他仿佛根本没看见眼前这群人,目不斜视,径直就要从他们身边走过。
“唐小子,站住!”
“耳朵聋了?给老子过来!”
吴用眉头一皱,感觉权威受到了挑战,提高了声调喝道。
唐骁却像是根本没听见,直接将他无视了个彻底。
他走到墙角那口破旧的水缸前,面不改色地将两桶浑浊的河水倒了进去。
哗啦——
水花猛烈溅起,发出的声响突兀地打断了院子里的训斥和阿谀,仿佛一记无声的耳光,抽在了吴用和秦通的脸上。
唐骁这彻头彻尾的漠视,瞬间点燃了吴用积攒的怒火!
他正愁没个软柿子来杀鸡儆猴,巩固自己方才的命令,这个一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唐骁就自己撞上了刀口!
“唐骁!”
吴用一声暴喝,声如破锣。
可唐骁还是一副完全没听见的样子,自顾自地挑起空桶,转身就朝门外走,连眼皮都没朝他抬一下。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于此。
吴用的胖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心中又惊又怒——这废物今天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当众落他的面子?
“好!好得很!”
吴用心头火起,恶向胆边生。
他那肥硕的身躯猛地往前一挺,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咆哮声夹杂着恶臭的唾沫星子劈头盖脸地砸向唐骁:
“狗娘养的小杂种!”
“老子问你话呢!是聋了还是哑巴了?”
“看来这几天没收拾你,皮是真痒痒了!”
“今天老子就给你好好松松骨!”
吴用一边咆哮,一边挺着硕大的油腻肚腩,气势汹汹地朝唐骁逼了过去,地面仿佛都在颤动。
话音未落,他那蒲扇般肥厚油腻的大手已高高扬起,带起一股恶风,用足了力气,照着脸就朝唐骁狠狠抡了过去!
他打定了主意,今天非要把这小子屎都打出来,揍得他跪地求饶、哭爹喊娘不可!
要让这墩里上下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清楚,谁敢忤逆他吴用,这就是下场!
就在那蒲扇般的巴掌即将落下之际,唐骁猛地抬起头,一股杀气迎面而来。
这一切,本就在他算计之中。
他忍了三天,摸透了吴用小人得志、刻薄寡恩的性子,最容不得旁人忤逆。
唐骁等的就是这个激怒吴用、让其主动出手并驳他面子的时机!
刹那间,吴用浑身一僵,仿佛被冰水泼头浇下。
他看到的哪还是那个唯唯诺诺、任他打骂的小卒唐骁?
那分明是一双见过无数死亡的眼睛,冰冷、漠然,没有任何情绪,却让吴用感觉自己像被猛禽盯住的田鼠,连骨髓都要被冻僵了。
“呃…你……”
吴用那扬起的肥厚手掌如同被无形的铁钳死死箍住,僵死在半空,进退不得。
他脸上的横肉不受控制地剧烈抽搐着,原本因暴怒而涨红的猪肝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片惊骇欲绝的死白,额头上瞬间渗出了豆大的冷汗。
死寂!
绝对的死寂!
整个火路墩的院子,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喉咙,陷入了彻骨的死寂之中,落针可闻。
秦通脸上那谄媚的笑容彻底冻僵,像是戴上了一张丑陋的面具。
赵良和马秋惊骇地张大了嘴,眼珠子瞪得溜圆,几乎要凸出来,完全忘记了呼吸。
就连一直躲在门后叫嚣的王氏,也猛地缩回了头,只敢露出一双充满了惊疑和恐惧的眼睛,偷偷向外窥视。
所有人心头都盘旋着同一个念头:
这……这个煞神……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唐骁吗?!
而另一侧,一直抱臂旁观的韩从,瞳孔骤然收缩!
他按在刀柄上的右手拇指猛地向上一顶,“咔”一声轻响,腰刀卡簧已然弹开!
他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变了。
从那个懒散看戏的边军老卒,陡然化作一头绷紧了浑身肌肉、发现了致命威胁的猎豹!
所有漫不经心瞬间消失,衣甲下的每一块肌肉都调整到最佳状态,进入了纯粹的临战姿态。
他锐利如鹰隼的目光,死死锁住唐骁的肩膀、手腕和腰胯,脑中飞速预判着对方下一步可能发动的所有攻击轨迹,以及自己该如何出刀,才能最快、最有效的格杀或拦截。
“好重的煞气……”
身旁的刘仲脸上的戏谑早已消失无踪,下意识地低声嘶了一口气,握着长枪的五指猛地收紧,指节发白。
韩从将唐骁抬头、眼神变化的每一个细微瞬间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绝不是一个普通墩军,甚至不是普通边军能有的反应!
那眼神里的冰冷和漠然,那瞬间爆发出的、几乎凝成实质的杀意,分明是经历过无数尸山血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后,才能融入骨髓的战斗本能!
更让他心惊的是,唐骁那看似随意站定的姿态,竟隐隐封住了从他这个角度发起进攻最便捷、最致命的几条路线!
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防御意识。
他也看不起吴用这肥猪,但吴用绝不能现在死,更不能死在他眼皮子底下!
否则,以北庄张管队的手段,追究下来,他韩从身为墩内战力最强之人,却坐视墩长被杀,绝对脱不了干系,到时候恐怕小命难保!
此刻的吴用他想咆哮!
想下令让所有人一拥而上,把这个该死的唐骁拿下,狠狠地鞭挞,踩进最污浊的泥地里!
可他的喉咙像是被那双冰寒刺骨、毫无人气的眼神彻底冻僵、扼死,一个音节都挤不出来,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更让他亡魂大冒的是——
不知何时,唐骁的手中已然握住那杆冰冷的长枪!
枪尖虽未抬起,但那姿态,宛若毒龙蛰伏,下一刻便要暴起噬人!
唐骁那双淬满了寒冰与死意的眼睛,更是如同锁定了猎物的洪荒凶兽,死死钉在吴用那张变幻不定、冷汗涔涔的胖脸上。
一股冰冷的、实实在在的死亡预感,如同毒蛇的信子,舔舐着吴用的后颈。
吴用有一种无比清晰的直觉,源自生物最原始的求生本能:
只要他再敢动一下,哪怕是动一根手指头,下一瞬,那杆长枪就会毫不犹豫地捅穿他的喉咙,让他血溅五步,横尸当场!
......
 苦瓜其实有点甜
苦瓜其实有点甜我擦,我怎么把章节名粘贴到这里了!
2025-08-27 11:05:20 ·广东评论 书友72373188
书友72373188请说读这本书的读者,个个帅过彭于晏,富过马斯克! 这是真的嘛?
2025-08-24 19:40:05 ·属地未知评论

